
古人对一些疾病的认识并不完全,如果事主又曾到过那些蛮荒之地,无知与偏见就会催生一个个志怪故事,这是古代的“地域黑”表现。志怪故事背后其实隐藏着科技史的细节,对真相不了解就会产生奇怪的说法。
中国古代有不少神异奇怪的事情,一些文人也热衷于记录这些事情。如何看待这些事情,是子虚乌有的想象,还是真实事件背后的误解,看看下面这个例子。
明代笔记小说《双槐岁钞》“蛊吐活鱼”条目下载:正统间,吴江周礼行货广西思恩,有陈氏女寡,返在室,赘为婿,凡二十年,有子,已十六岁矣。礼忽思归,妻不能止,置蛊食中,礼不知也,因令其子随之,默嘱之曰:“若父肯还,则与医治。”因授以解蛊之法。礼至家,蛊发,腹胀,饮水无度。其子因请还期,礼曰:“吾亦思汝母,奈病何?稍差,即行矣。”曰:“儿能治之。”即反接礼于柱上,礼告渴,以瓦盆盛水近口傍,欲饮,则掣去之。如是者亡虑数百次,烦剧不可当,遂吐出一鲫鱼,拔刺尚活,腹遂消。盖蛮中多有限年限月之蛊,稍逾期,则毒发不可救。故寡妇号“鬼婆”,人不敢近,旅客娶之,多受害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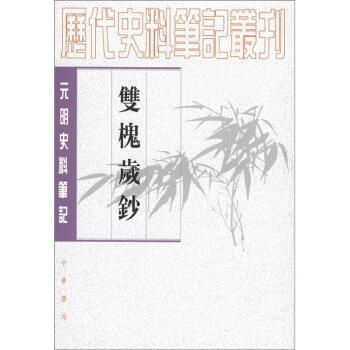
这本书也是挺正经的
阅读困难的同学看此翻译:明朝正统年间,吴江人周礼到广西思恩行商卖货。有一户陈氏人家女儿守寡,待在家中,周礼入赘为婿。过了20年,他们的孩子也16岁了。周礼忽然想回家看看,他的妻子不能阻止,就在饭菜中下蛊,周礼对此事并不知晓,他妻子便让孩子跟着周礼回老家,悄悄嘱咐他:“若你父亲愿意回来,就替他医治。”然后将解蛊的方法告诉孩子。周礼回到老家,蛊就发作了,肚子很胀,又不停地喝水。孩子趁机问周礼什么时候回去,周礼说:“我也很想念你母亲,可现在病了怎么回去?等病情好转,我们就走。”孩子于是说他能治。他把周礼倒着绑在柱子上,周礼口渴,则用瓦盆装水递到嘴边,准备喝到了又将盆撤走。如此反复多次,周礼居然从嘴里吐出一条活鲫鱼,而周礼的肚子也不张了。蛮中有定时发作的巫蛊,只要时间一过,就会毒发无可救药。所以寡妇又称“鬼婆”,普通人不愿接近她们,到那旅行的客人娶了她们,就容易受害。

这就是鲫鱼
看似是很可怕的事情,其实仔细剖析,并不可怕,因为其中有许多虚假成分,用史料参照就可以分析背后的猫腻。
《太平御览》卷七四三疾病部六“消渴”下收录了《后汉书》、《魏略》、《晋书》、《南史》、《唐书》、《拾遗录》、《交州记》、《淮南记》都有记载此类症状,即表现为饮水无度。
“瘕”下亦收录有诸多从《宋书》、《山海经》、《列仙传》、《续搜神记》、《异苑》、《志怪》中的例子,一个共同特点是人从腹中吐出异物,多为活物,有吐出蛇、白鳖、鸭雏,甚至死后令人剖其腹得一铜酒鎗。《龙鱼河图》解释:“大狗、鱼、鸟不熟,食之成瘕。”《易说》曰:“白露,气当至不至,太阴脉盛,人多瘕疝。”
如此,可以认为饮水无度和口吐活鱼是罕见的病,称为消渴和瘕。《双槐岁钞》将这两种现象同时发生认为是“蛊”在作祟。其实也不尽然。《续搜神记》有一病名“斛二瘕”,即是腹中异物每次好饮一斛二升的茶,多则不行。联系“蛊吐活鱼”中的例子,腹中是鱼,出现饮水无度的现象也是正常的,所以也可以视为就是一种病。而上述记录“瘕”的史籍中都未将其怪在巫蛊身上,只当成是一种特殊的病,而《双槐岁钞》认为是巫蛊的后果,则是因为主人公到了蛊术盛行的广西一带,受了思维定式的影响,也是带有一种“地域黑”的倾向。若依几例推敲,蛊术不是造成这个的唯一原因,其子受陈氏教授解蛊之法会治此病也可能是一种倒叙和想象的说法,赖在蛊术的头上并不准确。
虽然这则小故事是虚构出的“地域黑”,其中却有一个是确切的事实,就是入赘风。按常理,寡妇在中原地区应该要从一而终,以示贞洁。而当地的寡妇不仅可以再次嫁娶,而且是以女方为主导的入赘婚,这一点有别于中原地区礼制,也自然容易遭到嘲讽。这确实能体现当地的男女地位与中原地区推崇的男女地位有差别。有说法称这仍是母系氏族社会的遗存,但考察社会历史调查的资料,这种说法只是一种空想。
明正统年间的思恩,不知是前期在桂西北一带的思恩县,则今广西南丹、环江两县一带,还是后期的府治迁移后的思恩府,则今广西马山、武鸣两县一带,而不管确切指哪,寡妇再嫁和入赘之风在这里流行,上门郎享有继承岳家财产的权利,妻不生子可以再讨小妾,等到女方老人过世后可以随便回家。其责任是养老、埋葬岳父母。赘郎若是不务正业,干吹、嫖、赌、饮等坏事的,女方父母可以撵走他。入赘付的彩礼钱很低。
按说周礼是行货至此的商人,如果较富可以不必为了省钱而入赘至寡妇家,当然如果真爱也没什么说的,但真爱又怎会担心一方不愿回来然后暗中下蛊呢?周礼可能是行货至思恩入不敷出破产了。因为不管思恩县还是思恩府,这些地方的土著居民都因语言不通或没有需求而不习惯商业活动,到这里做买卖,破产是很有可能的,剩余盘缠不够返乡,为了生存而选择入赘至寡妇家中,并期望继承岳家财产,再行商。周礼在此生活二十年,也没干什么坏事,还生了一个儿子。大概是岳父母都过世了,他有机会回家看看,这都是很正常的行动,为何会遭其妻毒手?
按常理应是周礼长时间不回才蛊发,何以刚至家就发,如此严苛有违人情。礼曰:“吾亦思汝母,奈病何?稍差,即行矣。”可见周礼刚至家就蛊发,并没有说是因他留恋家中亲友而迟迟未归(若有这种想法也确是人之常情),但此时蛊发就算有心想回去与陈氏度日,也因陈氏这一蛊而造成行动不便,陈氏的做法实在有违常理。且在《岭外代答》中记载,岭南妇人虽善于制蛊,但是常人都有预防和破解之法,这些方法也无需什么特殊的材料和仪式。周礼在此入赘并生活了二十年这么久,不知道如何防备蛊毒,并且都不知道自己中的是蛊毒,这也说不过去。

当然不是吃这种东西中的蛊
若说是病,确实有一种病可以解释——吃鱼生因寄生虫患病。东汉末年的张仲景在《金匮要略》就指出,“食脍,饮奶酪,令人腹中生虫,为疟”。几百年之后的南北朝时期,陶弘景也警告食脍可能有害,流行病刚痊愈的人不能吃,否则会引起拉肚子。不过,很显然,直到隋唐时期,众多吃货并没有将这一告诫放在心上。因为贪食鱼脍导致得病的人实在是史不绝书。有病就得治,病人多了医生也难办,所以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就非常明确地警告国人:“肉未停冷,动性犹存。旋烹不熟,食犹害人。况鱼鲙肉生,损人犹甚。为症瘕,为痼疾,为奇病,不可不知!”这不啻在传统医学(中医)上为淡水鱼制成的生鱼片宣判了“死刑”。
但近现代的两广地区,堪称古老的“(淡水)鱼脍”如活化石一般存在。明朝的徐霞客在游历到广西地区时,就发现当地“乃取巨鱼细切为脍,置大碗中,以葱及姜丝与盐、醋拌而食之,以为至味引”。现代广西的汉族、壮族和侗族都延续了食用“鱼生”的习俗。《广西通志·民俗志》记载,“生鱼片,壮、汉、苗、侗等民族的传统菜肴,先用三至五斤重的鲜活草鱼或鲤鱼,刮鱼鳞洗干净,除去内脏,取出骨头,将肉切成片,然后拌上糖、醋、酒、盐、姜、蒜、酱油、花生油等,略为腌制,即可食。其味道鲜嫩香甜。”《上林县志》也说:“上林汉、壮群众遇贵客来临……视‘鱼生’为上品佳肴。”至于今天隶属于广西首府南宁的横县人更是将横县鱼生称作当地的“县菜”。清代《横州志》就记载:“剖活鱼细切,备辛香、蔬、酶下箸拌食,曰‘鱼生’,胜于烹者。”

横县鱼生
只可惜,“鱼生”固然美味,风险依旧巨大。现代科学研究表明,很多淡水鱼中有一种非常顽固的寄生虫——肝吸虫,多达30多种淡水鱼可成为肝吸虫幼虫的中间宿主。生食或食用未充分加热的含有肝吸虫的鱼后,其成虫寄生于人的肝脏、胆管内则会导致肝吸虫病。这种虫子可以在人体内生存长达二三十年。而且,被感染后不易察觉。
但这种情况往往又和巫蛊联系到了一起。偏见与无知混合,就产生了这样一则小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