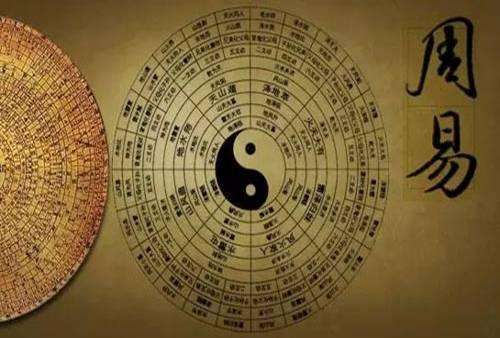
《周易》被誉为群经之首是凭借其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而不是卜筮之法。卜筮之法只是一个媒介,其背后是中国的传统的自然和谐的世界观。六十四卦只是一个参照,在人们不知所措的情况下为人们提供建议和指导。
《周易》是中国传统“六经”之一,被誉为群经之首,对中国的文化传统影响巨大。“周”有几重意思,一是成书于周;二是周全、完备的意思。易也有多种解释,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东汉郑玄的著作《易论》中认为“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这句话总括了易的三种意思:“简易”、“变易”和“恒常不变”。他认为宇宙间的万物可以用易来概括是因为他们都顺其自然,表现出一种简易的性质,同时它们在不断的变化,但又保持着一种相对的不变的恒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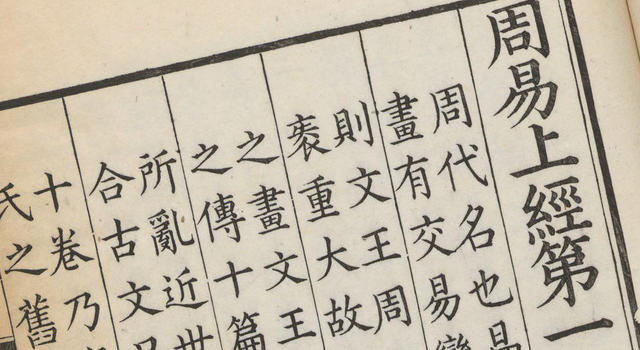
《周易》最初作为卜筮之书,记录了先秦的卜筮之法。《周礼》曰: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周易》可能只是先秦卜筮之书的其中之一,但另两部已经失传,故而周易的价值突显,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周易》是研究先秦卜筮不可绕过的一部著作。对于《周易》的作者也众说纷纭,有伏羲、周文王、孔子等说法,即《汉书·艺文志》在描述《周易》的成书过程时,称的“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根据现代学界研究,一般认为,《周易》为周初周人所作,重卦出自文王之手,卦爻辞为周公所作,孔子作“十翼”。
自孔子赞易以后,《周易》被儒门奉为儒门圣典,六经之首。儒门之外,有两支易学与儒门易并列发展:一为旧势力仍存在的筮术易;另一为老子的道家易,易学开始分为三支。
由于古时的人们对自然界和社会的发展缺乏明确的认识,从甲骨文的占卜活动中发展出卜筮之法,而早期的这种卜筮之法又确实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一些指导性意见,使得人们能够也愿意去运用这些卜筮之法,故而人们在普遍智力不高的情况下对卜筮之法依赖颇深。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几派的易学思想不断交融,使得《周易》不仅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还发展出一系列依赖于《周易》的卜筮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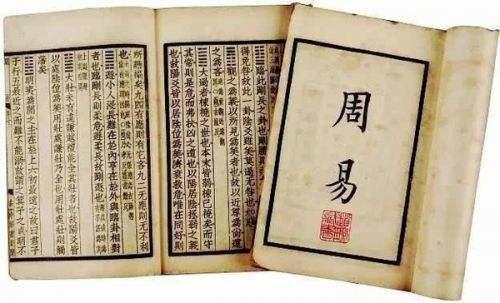
然而在近代,西方的科学思想传入中国,民智渐开。由于《周易》中蕴含的内容和精神极为广博和玄妙,而普通大众对其不甚了解,对《周易》的印象停留在“算命”这些实际行为上,一些不学无术之人的滥用,加之批判传统糟粕的潮流影响,使得人们对《周易》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误解,这些卜筮之法被斥为封建迷信的骗人把戏,使得《周易》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回顾历史上《周易》中卜筮之法的运用,可以看到它虽然不是百分之百的精确科学,但也有其独特的魅力。
《左传》中不少运用《周易》的记载。关于《左传》与《春秋》的关系,有不同说法:有说两书是相互独立的著作,也有说《左传》的成书是为了解释补充《春秋》。但不管采哪种说法,《左传》对于记载春秋时期史事的价值是不变的,在《左传》中有不少卜筮的例子,都可以体现当时的人们对于《周易》的使用已经达到了一种较为普遍的程度。
《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记载:
陈厉公,蔡出也,故蔡人杀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与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光远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风也;乾,天也;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故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庭实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宾于王’。犹有观焉,故曰其在后乎!风行而著于土,故曰其在异国乎。若在异国,必姜姓也。姜,大岳之后也。山岳则配天。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
周史运用《周易》为陈国的敬仲卜了一卦,结果预示陈国将会衰落,敬仲的后代将在姜姓之国(即齐国)称王。事实正是如此,敬仲的后代出逃至齐国,改称田氏,即后来的“田氏代齐”。可见周史的预判是很准确的。但观察这段记载并比较《周易》的卦象会发现,观卦之象为上巽下坤,而否卦为上乾下坤,引文前半部分是对此三卦的描述,后半部分又出现了一个“山”,而“山”是艮卦之象,艮卦并不属于上述三卦中的一卦。

这是因为,《周易》在诞生之初对主要功能是用于卜筮,而在原始的卜筮过程中,解读的依据在于“象”,以及根据“象”推导出的某些文辞。胡适在其《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就说《易经》只有三个基本观念,一是易,二是象,三是辞。“象”就是模仿,类似的意思。胡适十分强调“象”的价值,认为我们的器物制度乃至一切事物都产生于我们对自然的模仿。
“象”在卜筮中的价值重大,因此为了让自身的解说更具有说服力,也为了增加解读的空间,古人在占算的过程中,发明了所谓的“互体”之法,这也是春秋时期的一种独特的取象方法。这其实从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周易的卜筮之法并不是完全依赖于呈现出的卦象,而要由解释的人根据他的才智去创造出能解释出符合现实的预言的“象”。
《周易》的八卦企图囊括了天地万物,八卦重叠产生的六十四卦更是将这一范围扩大,世间的事物都包含在其中,因此《周易》在编撰之始就相当于一个“智囊”,替世间的各种情况都想好了对策,卜筮者则需要根据现实情况去判断,现在应该是哪一种情况,应该做何抉择,仿佛现代的计算机程序,输入不同的指令便会运行相应不同的程序。但这也正是卜筮的难处所在,得到一个卦象不难,难就难在如何去解释它,这才是体现卜筮者是否掌握《周易》精髓的地方。
《周易》对人们来说犹如一面镜子,可以从它的卦辞中对照自己的处境,从而判断自己应该怎么做。因此卜筮之法不一定只有一种,除了专业的史巫,部分知识分子其对于《周易》本身也存在了解,但其理解的角度多不同于史巫。这样的事在《国语》《左传》中都有记载。
《国语·晋语》记载:
公子亲筮之,曰:“尚有晋国。”得贞屯悔豫,皆八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闭而不通,爻无为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不有晋国,以辅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晋国’,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国之务也,吉孰大焉!”
从这个例子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两方对同一事件的解读是不一样的,那么在预测上这次卜筮已经没有了意义。所以也证明卜筮不是万能的,还是要依靠自身的判断,卜筮只是一种工具,它体现的只是一种指导价值,不能将其作为最后的决策依据,过分的强调《周易》的普适性称不上是了解《周易》。迷信工具的坏处就是只流于表面,而忽视了工具背后所蕴含的精妙道理。
并且《左传·襄公九年》还有记载:
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
穆姜将占算人的品德与卜筮本身进行了关联,引出了相类于后世的“易为君子谋”的卜筮原则,从而将道德属性凌驾于卜筮本身之上。这一变化突出的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周易》使用态度和方法上产生了不同见解,一些人将人生日用之理与卜筮功能结合,在运用《周易》进行占算的同时,将卜筮本身的解释与《周易》自身的文辞相结合。这也预示着《周易》不单单是一本卜筮之书,它其中蕴含的哲理也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周易》之所以能用六十四卦将世间万物囊括在内,离不开其抽象的哲理。而现在对于《周易》的运用却忽视了其中的哲理,这既是文化的损失,也是导致其处于尴尬境地的原因之一。《周易》及其背后的深邃哲理从未标榜包治百病,而使用的人对于它未能满足自己的需要便将其贬得一文不值,这不是《周易》本身的责任。
可以看到,《周易》之所以被誉为群经之首,具有引导的作用,是凭借其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而不是卜筮之法。卜筮之法只是《周易》中思想具体表现的一个媒介,其背后是中国的传统的自然和谐的世界观。卜筮之法的预言从来都是劝人行善或顺天而行,随着 “象”与“辞”的引导而顺应自然。《周易》事先设计好的六十四卦虽说包括了世间万物,但它只是一个参照,在人们不知所措的情况下为人们提供一个建议与指导,但具体采纳何种建议还得靠自己的判断。先秦时期的贤人能为后世这么多种可能性,固然与他们的聪明才智相关,也与“易”的三个内涵有关,世事经过了沧海桑田的变易,但世间的道理不会改变太大。参透了《周易》中的道理,没有卜筮之法也能游刃有余地处理世事。
明确了这些,对《周易》、卜筮的误解就可以消除了,我们也该用理性、客观的态度去认识它们。
参考文献:
高怀民:《先秦易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美)夏含夷:《是筮法还是释法——由清华简重新考虑筮例》,载《周易研究》2015年第3期
刘震:《清华简与筮例比较研究》,载《周易研究》2015年第3期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商务印书馆,2011年
邬国义等:《国语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