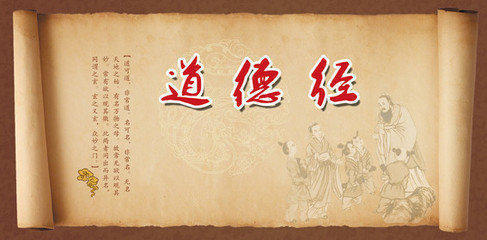
《老子》本身对科技的态度的复杂性导致了其思想对古代科技发展所造成的影响也是复杂,不能一概而论。《老子》中的经验主义、无为思想、熟能生巧、阴阳观念、反对智慧等都影响了古人,也影响了科技创造。
李约瑟曾评价儒家一方面它助长了科学的萌芽,一方面又使之受到损害。因为儒家思想是重理性的,反对任何迷信以至超自然形式的宗教;但儒家思想把注意力倾注于人类社会生活,而无视非人类的现象,只研究“事”,而不研究“物”。因此,对于科学的发展来说,唯理主义反而不如神秘主义更为有力。[1]而他所说的神秘主义就是道家思想。
早期的道家思想与气质很符合科学,道家就像原始的科学家。他们是出世的,希望研究自然。道家思想在先秦时期的著作中蕴含着重要的科学思想,道家静心观察自然、践行不违反自然的“无为”、认为“道”无处不在、道家的经验主义、庄子的齐物论思想、老子的因果论等思想都与现代科学思想不谋而合。从文化相似性的角度看,西方文明能发展出的科学思想,东方文明也可以。道家或许就保存着中国原始先民观察自然的观点。
已有学者总结老子思想对中国传统科技文化的影响有三个层面,一是神秘主义色彩的“道”的观念,二是“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三是重直觉了悟的思维方式。[2]以及老子科学思想基础的自然观,包括以“道”为始基的自然哲学、宇宙生成论、宇宙循环论,由此发展其技术思想从“朴散为器”到“大制不割”,从“有而用之”到“有而不用”,从“有之以为利”到“无之以为用”。[3]这些对《老子》思想中影响科技文化的论述均较为抽象。众所周知,历代流传的《老子》版本众多,有些解释尽管精妙,但对当时从事科技工作的普通人来说也许闻所未闻,本文对于存在争议或多种解释的文句尽量选择最通俗的解释,选择最“大众化”的解释才能更贴切思想流传的规律,如葛兆光所说“一般的知识与思想”[4]。本文以《老子》为基础,结合一些古代科技实例,探究其中哲学思想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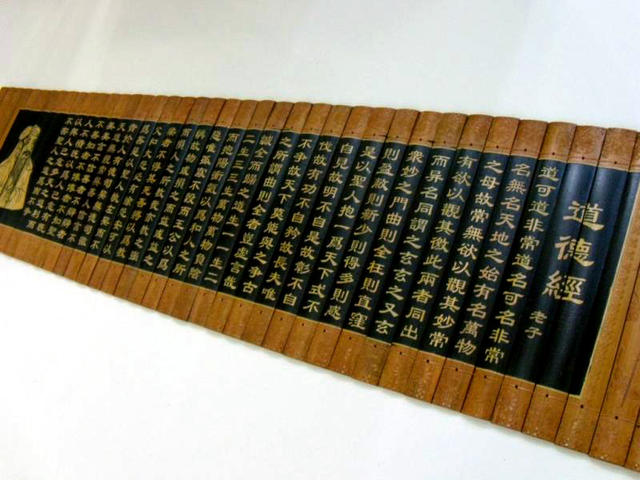
总的来说,《老子》对道的阐述给人一种玄之又玄的感觉。一般来说,人们对科技的探索和使用源于模仿自然界中的事物,如传说鲁班观察叶子的边缘发明锯子、观察荷叶发明雨伞。而“道”在一般情况下也是指自然规律,《老子》明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以探索“道”的道家很像原始的科学家,只有他们能说清自然界里种种神奇的现象。
但《老子》第一章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般解释为,道不可以言说,也不能给它下一个准确的定义。这种对道的玄之又玄的说法令大多数的人看来,“道”是他们捉摸不透的东西,是不可能说清楚的。
第二十五章也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像老子这样的圣人都不能说清这个东西,普通的人们知道天地间有“道”存在就足够了,没有必要花时间去琢磨。这样一来,社会上只有少数人去探究自然界的规律,也就少有人去研究自然事物之间的理,更遑论研究出较为深入的结果了。在这样一种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古代极少有谈论自然事物间“科学道理”的情况,更多的是一种对过往及自然的直接模仿,是一种经验主义,所以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只有技术没有科学。
虽然《老子》给道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但也有不少人因为存在这种神秘感而受到鼓励,去观察自然。在《老子》的文本中,虽然存在关于“道”说不清的论述,也有鼓励去观察“道”的论述。
《老子》第十六章曰“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一方面,老子承认“道”是复杂的,难以说清的;而另一方面,他还是主张,要多多观察世间万物,从中窥探“道”的奥妙。而在这一层面上,《老子》还提出两个有利于科技发展的重要的特质——“无为”和“静心”。
第二章曰:“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此章意在说圣人应该处于无为的境地,而不去刻意地表现,钻研科技也要顺应“道”,不去卖弄奇技。而古代一些合乎科学的现象却因此被视为奇技淫巧。《博物志》卷四记载了一些“戏术”,如其载“烧白石作白灰,既讫,积著地,经日都冷,遇雨及水浇即更燃,烟焰起。”[5]这些其实背后有其科学依据的行为被视为戏术,而不是应该探索推行的正道,便是由一种“无为”的思想在阻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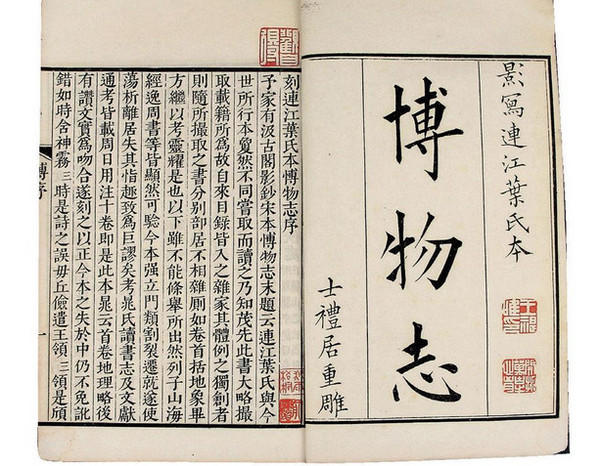
《博物志》、《搜神记》等志异小说中不少奇闻异事用现在的思维去看都是有科学道理的,而当时却被视为“异”。联系这些志异小说成书的时代,正是玄学盛行的时期,《老子》中的思想既让人们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又将其视为怪事。
第六十三章曰:“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第六十四章云“为之于未有,治之于为乱。”都意在讲究在事物还未形成时去处理,就能尽比较小的力量,造成比较大的影响,同时又能顺应事物发展的规律,以此达到无为的效果。同时,要达到顺应事物发展规律这一要求,事先需要知道事物是如何发展的,这也离不开对自然的观察。
这一点上则启发了众多的科技成就从小处着手,促成了古代众多“精巧”的设计。然而,在这一点的运用上,人们又会因为习惯了去顺应自然,而不会主动做出违背自然的事,在没有重大生产需求的推动下,这也使得中国古代科技发展较为缓慢,因为一直以来都顺应着自然而行动,满足了基本的需要,其他的危机又多被扼杀在萌芽中,难以出现一个突破式发展的契机。这也养成了中国古人对一些基本技巧的娴熟使用,形成影响巨大的经验主义。
第十二章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老子反对过度的享受,追求清静的态度,观察万物之道的前提就是“致虚极,守静笃”。儒家教导人们要积极入世,为现实政治而努力,而老子反对那种入世的主张。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和工匠们在传统官僚社会中的地位较为复杂,其中不乏高级官员、王侯宗亲,但最大的发明家群体还是平民、技师和工匠。[6]
入世或进一步入仕的行为对他们来说可能是衣食无忧后不屑一顾或是奋斗终生都难以实现。这种情况下,老子主张的清静对于他们这些隐性的或专职的从事科技工作的人们来说便显得重要,静下心来认真细致地观察钻研才能得到成果。
而长期对自然的观察,也可能不会促进自然科学的产生,反而产生了经验主义。因为长期的观察自然过程中,如果没有深层次地理解这一现象背后的机制,容易想当然地理解为“它一直都是这样,以后也还是这样”,中国古代近千年的农耕社会环境,与自然密切相关的便是农业耕种、天文历法、水利灌溉、纺织、冶金这几类,而它们也都可以用经验来操作。久而久之,这些行业内的探索就不是科学,而是取决于技术的熟练度。
二十七章曰:“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善数不用筹策,善闭无关楗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老子推崇这些熟练的行为,将一些看似做不到的事情认为是熟练之后自然而然的事,能将一种技能运用得熟练之极的人往往也是一种圣人。
这大概是道家所共同推崇的,《庄子》中也有运斤成风的匠人形象。也因为此,中国古代许多科技成就,往往不是仔细研究背后的原因,而都认为是熟练的结果。
如杨宽先生在《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中论述的冶铁技术的发展历程,众多冶铁成就的出现并不是因为古人真正认识到了现代所说金属冶炼中的化学反应,而是将选料、鼓风、煅烧、捶打这些基础工序进行不断地实践、改进。现在看来,古代工匠们能冶炼出优质的钢铁是因为选用了优质的矿料、鼓风充分致使燃烧充分,锻打后含碳量适当。而在当时,时人普遍认为之所以出现质量上乘的铁质材料都是因为工匠们“善治”,换作一个平庸的匠人,就算给他这些材料他也无法造出这种优质的钢铁。

而《老子》中的阴阳等相对的观念也对古代科技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第六章曰:“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緜緜若存,用之不勤。”
第二十八章曰:“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为天下谿,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
第六十一章曰:“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为下。”
这些言语中提到的女阴、雄雌、牡牝形象,李约瑟对此有相关论述:“这种对女性的强调象征着道家所特有的对待自然的容受态度。道家研究自然所持的态度是女性的,即研究者不能以先入为主的观念来对待自然。道家懂得这种没有偏见的中立态度,他们以谦卑的态度提出问题,以谦卑的精神面对自然。”[7]
与此同时,阴阳、雄雌这种相对的概念反复地提及并用来论述天地间的万物之道,古代从事科技的人们也常常认为他们发现或发明的某种现象、事物可能就是天地间阴阳相交而生的产物。王充《论衡》中曰“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8]。在这种先验的观念影响下,古人的科学思维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制约。如《天工开物》中称“夫金之生也,以土为母,及其成形而效用于世也,母模子肖亦犹是焉。”[9]便是将金属视为子,土石视为母,母生子乃天经地义的事且子与母相肖。再如《天工开物》解释灌钢法时说“火力到时,生钢先化,渗淋熟铁之中,两情投合”,[10]杨宽先生解释其意为将生铁比为男性,熟铁比为女性,生铁与熟铁两情相投,就产生了钢铁,如同男女繁衍生子的道理。[11]这种观念以现在的认识来看无疑是错误的,但是在《老子》思想的长期影响的背景下,又是合乎情理的。

《老子》八十一章中蕴含着各种层面的论述,确实像李约瑟所描绘的那样,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确实具备原始科学家的特性。但是,《老子》中又存在着一个十分明显的、很不利于科技发展的倾向——反智主义。
第三章曰:“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
第十九章曰:“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第五十七章有言“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第六十五章云“民之难治,以其智多。”
第八十章曰“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也一直成为《老子》的代表思想之一。
这些反对智慧创造,反对“利器”“技巧”,并且主张过着较为原始朴素的生活的思想在一些学者看来是因为老子是原始奴隶主阶级因而留恋较原始的生活。不管其动机如何,《老子》作为一部经典流传下来,其思想对古人的思维、行动造成了影响是确定。科技工作者自身既然从事了这一工作,自然不会将《老子》这一思想视为真理。
而一部分受《老子》思想影响的人虽然不是科技工作的直接从事者,但他们对科技所秉持的态度同时也会反作用于科技事业,政府官僚的作用尤为明显。如古代从事这些科技工作的人都被视为末流,这与传统的官僚政治体制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它把全国的知识精英都吸引到了文职系统中了。然而,那些精英们接受过《老子》思想的影响,他们则主张将工匠与商人视为末流,以便加强统治。缺乏了商业活动对科技创造的需求与鼓励,缺乏了工匠应得的支持与地位,大部分科技成果只能限制在政府所需要的领域内。
又如古代手工作坊有民营与官营之分,为了不让百姓掌握“利器”,政府会将一些杰出的匠人抽调至官营作坊,并编订户口,世袭该职。这一方面有利于众多杰出的工匠聚集在一起,对科技工作能有精益求精的创作,然而这也是政府的一种垄断行为,掌握在政府手里的科技成果与民间的科技成果缺乏联系,产生了断层,也可能造成一些成果的失传。这便是据史籍记载古代有一些科技成就十分突出,而后世却不见其痕迹。
而我们现在回顾的一些古代杰出的科技成果,也不完全是纯技术成就,有一部分是其他创造的副产品。如火药就不是工匠、农民或石工发明的,而是来自道教炼丹家。前文也曾赞扬道家和道教具有原始科学家的特质,然而火药这一发明不是道教炼丹家专门从事的,而是炼丹伏火中的副产品。因此,有许多现在认为的杰出成就在当时可能是受到反对的,但它蕴含在其他成就之中因此不为时人关注。

总而言之,老子中对科技的态度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
这与它的时代性有关,《老子》成书于春秋时期,各种名物发展都还在起步阶段。葛兆光认为,老子一系道者其实也在寻求一种秩序,只是他们在寻求秩序时,依据的是他们曾作为史官的更为熟稔的宇宙秩序,以及更易理想化的古代世界。[12]不能苛责它能为之后几千年的发展都作出恰当的论述。
再者与《老子》的体例有关,它是一部格言式的著作,其所处时代是个变动的时代,各种社会现实的出现造就了多种观点相交融,对方方面面都有涉及,既有赞扬肯定科技价值的,又有对知识的否定。朱亚宗评论道,一言以蔽之,老子的科技价值观是以否定性为基本特征的文化保守主义的科技价值观。再进一步则可以说,老子虽然深通自然奥秘,懂得科学技术却并不看重科学技术。[13]
《老子》强调无为,重视静心并关注自然,但造成了经验主义,使人们把问题归结于对一种基础技术的熟练程度。与此同时,《老子》本身对“道”秉持着一种玄之又玄的神秘主义,令人望而却步,并反对智慧,反对奇技,主张过着简单朴素的生活。
《老子》本身对科技的态度的复杂性导致了其思想对古代科技发展所造成的影响也是复杂,不能一概而论。且对科技的论述也不属于《老子》思想的重点。中国古代众多典籍都对科技发展有过论述,篇幅也长短不一,《老子》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不能夸大其影响。
注释
[1]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2页。
[2] 刘睿、李锋:《老子思想对中国传统科技文化的影响》,载《中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3] 陈红:《老子科学技术思想研究探微》,载《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4] 指的最普遍的、也能被有一定知识的人所接受、掌握和使用的对于宇宙间现象与现象的解释,这不是天才智慧的萌发,也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当然也不是最底层的无知识人的所谓“集体意识”,而是一种“日用而不知”的普遍知识和思想。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4页。
[5] (晋)张华:《博物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8月,第23页。
[6] (英)李约瑟:《文明的滴定》,商务印书馆,2016年8月,第13~17页。
[7] (英)李约瑟:《文明的滴定》,商务印书馆,2016年8月,第146页。
[8] (东汉)王充:《论衡》,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77页。
[9] (明)宋应星:《天工开物》,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4月,第221页。
[10] 同上书,第348页。
[11] 杨宽:《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5月,第262页。
[12]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卷一》,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26~127页。
[13] 朱亚宗:《老子科技观述评兼与李约瑟先生商榷》,载《船山学刊》199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