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一段时间疫情在欧洲和北美爆发,西方疫情现状让中国网民产生一些共同的疑问:为什么那些西方人似乎“不怕死”?他们为啥不戴口罩?他们为啥还到处乱跑?他们为啥还没有停工停学?他们为什么不能“抄中国作业”?
来源:严肃的人口学八卦
作者:李婷(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副教授)

图片来源见水印
有一些很好的文章已经从制度文化、政治体制、医疗理念、国家资源等方面进行了解释。在这一篇推文中,我们想从中西方生死观差异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
死亡本身是一个生物属性,但是人所具有的社会属性使得同样的死亡事件,投射到不同的文化观念上就形成了具有显著差异的生死观。
其实中西方在生死观上的差异很早就在历史中得以体现,比如中国对航海事业最早的尝试是为了寻找长生不老药;而西方的大航海时代则主要是为了贸易和资源而开启的。
又比如,同是前化学时代,中国人痴迷于炼丹,而西方人则醉心于炼金。伟大的科学家牛顿甚至将其后半生全部投入到炼金活动中。
再比如,养生文化已经在中国历史中绵延流传了几千年,伟大文学家苏轼便是养生界的先锋人士,到今天更是随着父母们的手机渗透到了几乎每一个中国家庭。
而在西方,养生这个词对他们来说就是黑人问号脸。这些对比似乎都在说明一件事情:中国人爱命,西方人爱其他,反正没那么爱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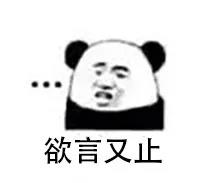
如果要理解中西方生死观的差异,就要回到各自的文化基础之中。
中国生死观的文化基础
在历史中,中国社会的价值体系主要建立在 “儒释道”三家之上,而其中的儒家文化和道学道教更是发源于本土。
儒家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调入世,关注人生的现世意义。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他的本意是要人们务本求实,关注现实生活,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于对生命社会价值的追寻,而不要分心去思考死亡及其之后的世界。
这种生存哲学一方面引导了民众对现实的责任,而另一方面也将死亡问题排斥在了中国的日常话语体系和生命视野之外。
这便成为中国人忌讳死亡,恐惧死亡的文化根源之一。因为“死”就意味着世俗生活的彻底破灭,这对于注重现实意义的中国人无疑是沉重的打击。

虽然与儒家学说具有浓厚的现世伦理主义的理念不同,道家学说崇尚自然主义的生死观同样具有重生轻死的倾向。
在老子和庄子之后的道教一方面继承了重生轻死的价值观,另一方面构建起了一套神仙体系思想,将虚构的自然主义生死观改造为现实主义的对长生的追求,并企图从逻辑的角度证明神仙的存在以及人类长生的可能,由此揭开了中国人民长达千年的炼丹养生之路。
在儒道两家的深远影响下,中国人民形成了畏惧死亡,积极求生的价值观;“好死不如赖活”的信仰也深深扎根在了民间。
这种思想也成为当代中国人卫生实践的基础。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预期寿命的增长大大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除了制度优势和性别平等的红利以外,也来自于自下而上的积极健康实践。
在新冠疫情下,中国民众牺牲自由、生计和娱乐,自主在家隔离将近2个月,除了政府和社区的高度组织性、个体的集体主义意识,也与大众对死亡风险的高度谨慎和“求生欲”有关,也才会出现举报欲来窜门的亲朋好友、举报隔壁疑似代购等”迷惑”行为。
一些美国的朋友一直认为中国人在疫情下的行为都来自政府的高压政策,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我们都是自愿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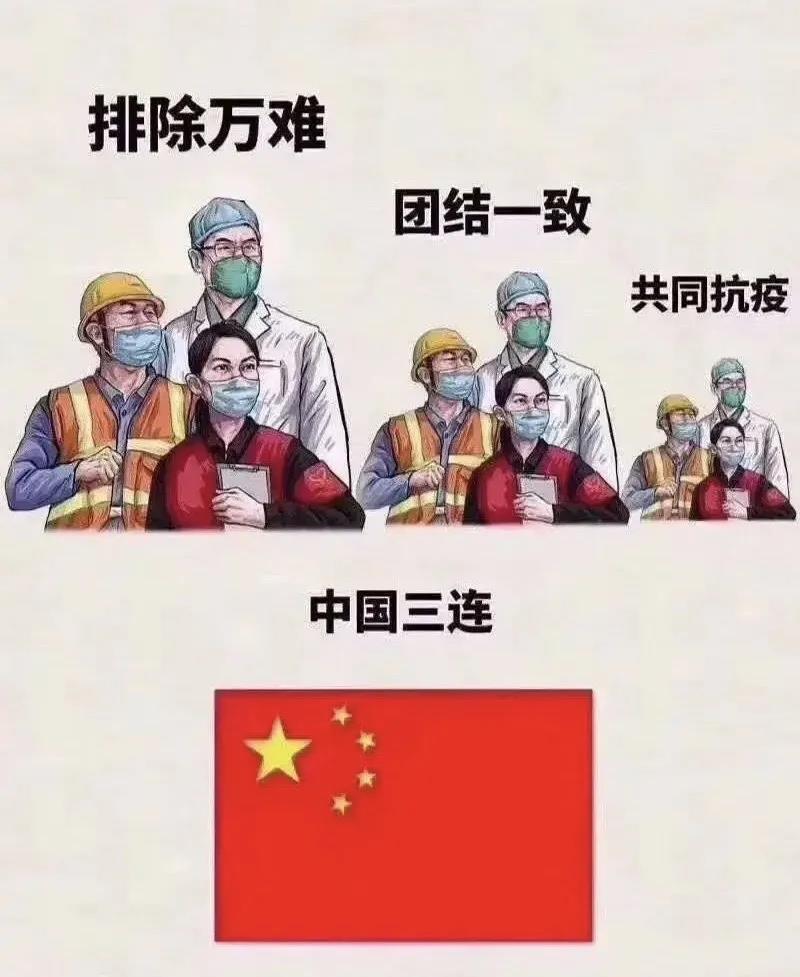
在东西方分歧最大的戴口罩上,也可以体现出东亚文化中这种高度谨慎性。不管口罩能否真的阻挡病毒,戴口罩这个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构建起了我们自身的心理安全感,也重建了陌生人之间的信任感。
这种对生存安全感的高度需求,是西方人无法理解和体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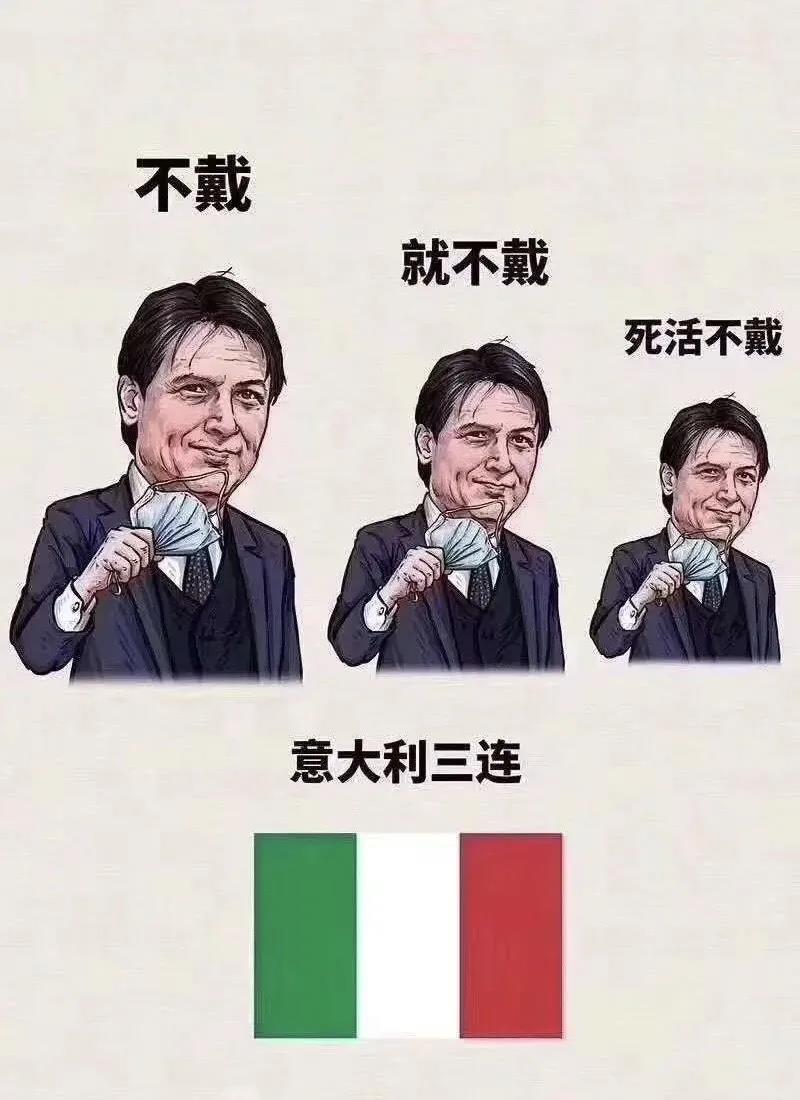
应该说,整个东亚文化圈的民众在自下而上对疫情进去阻断的过程中,起到了更好的效果。
西方生死观的文化基础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西方生死观的文化基础。如果说儒道文化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价值观,那么西方人的文化底色就是古希腊哲学和基督教。
自古希腊开始,死亡就是哲学家最常谈论的议题之一。他们非常注重对死亡本性的追问和在精神上对死亡现象的超越。
很多古希腊哲学家把人看作是灵魂与肉体生命的结合,灵魂高尚,肉体肮脏。柏拉图认为灵魂永恒,独立于肉体又赋予肉体以思想和智慧。这些哲学家都将死看作物质生命的精神升华,那么肉体的死亡就并不代表个体意志的消失,也就没什么值得担心和恐惧。
于是苏格拉底才会在留下那一句经典的“不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之后从容求死。

此后的基督教更是将死亡提升为达到新的生命的途径,通过追求以上帝为精神象征的终极价值, 来建立个体的生存信仰体系。
人们在现世的行为是为了摆脱尘世间的罪孽,实现世俗生存的价值,从而在死后得到救赎,以达到永生的境界。
同时,基督教文化中很早就有“原罪”的概念,它来自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的警示,时刻告诫人类不要突破自身本能的极限。而追求无限的生命就是其中一项禁忌。
虽然宗教色彩在西方世界中越来越淡化,但是对死亡相对淡然的态度也仍然扎根在了个体意识之中。这种淡然不是真的不怕死(应该说没有人不怕死),而是他们对死亡风险的警惕性远远低于我们,或者说警报阈值比较高。
他们大概会认为如果出去工作,参加聚会活动的风险很小,那么就不应该放弃正常的生活和娱乐,也会倾向认为很多事情比可能的死亡威胁更重要。而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如果存在一丝患病和死亡风险的行为,都是应该避免的。
西方国家作为疫情的“后发”国,在拥有较充分信息的情况下,一开始的漫不经心也多少源于对死亡风险的低警惕性。

最近被频繁提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也与西方人的传统生死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个理论将达尔文的进化论引入到社会理论中,强调生存竞争所造成的自然淘汰在人类社会中也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并对其进化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当今世界,社会达尔文主义显然是政治不正确的,但是在西方社会它仍然有不小的影响力,特别是在精英人群中。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最近提出的人群免疫应对法,就被认为带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色彩。这些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本质上也是缺乏对死亡的恐惧与敬畏。
对比中西方的生死观,并不是为了证明哪一种观念更好更现代。
我们需要认识的是,不同社会中个体的行为有很多都根植于其长期形成的价值观念系统中,不了解也不应该嘲笑。也如开始所强调的一样,生死观只是解释中西方在应对疫情中个体行为差异的一种视角,所有的文化、制度、政治因素都是不可分割的。
中国式抗疫在疫情控制中已经取得了初步胜利,那么西方式抗疫结果会怎样?他们会在多大程度改变行为模式?我们拭目以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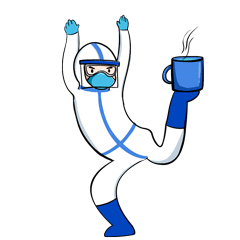
参考文献
1、宋晔. 中西方文化中的生死观及其教育启示[J]. 思想理论教育(上半月综合版), 2003, 000(007):28-31.
2、李高峰. 中西生死观之比较——基于文化差异的视角[J]. 中国教育与社会科学, 2009(10):23-24.
3、刘魁, 许小峰. 中西生死观的文化比较与生命伦理反思——兼论未来科技文明的发展趋向问题[J].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2).
4、赵晖. 生死观上的人类智慧——中西生死观比较[J]. 学理论, 2009,(28):93-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