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个新作品仍然只是窦唯对于个人小世界的刻画。
有人说窦唯从未避世,他一直在用音乐关心身边的人。这样的说法似乎又因为他最近发布的作品《后疫》而得到了进一步佐证。如同歌名所暗示的那样,这首 39 分 46 秒的音乐作品是对于近期新冠疫情的刻画,因此人们欢呼窦唯并不像他那个为人所知的绰号“窦仙”所暗示的那样高高在上,窦唯始终与普通人站在一起。
这或许只是人们的一厢情愿,一种希望自己仰慕的人与自己站在一起的心态。事实上,《后疫》这张专辑展现的是窦唯一贯的冷淡、疏离、甚至是超脱的态度。在曲子最开始的长达 30 多分钟的时间里,一直如此。

作品的封面也是窦唯一贯的风格
从结构上来看,《后疫》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创造氛围的电子合成器、窦唯近年来广泛适用的民族乐器、以及来自疫情期间的各种声音采样。整体上,前两者交替出现构成了曲子可以聆听的主要组成部分。
氛围电子合成器的运用大量出现在科幻电影当中,用以描绘一艘庞大的宇宙飞船孤独地穿梭着更为浩瀚的宇宙空间中。只有微弱的电子音,成为人类茫茫旅途中唯一能够提示时间和空间感的标志。《后疫》最开始的氛围段落,甚至可以直接挪用到科幻电影中作为配乐,都不会有丝毫的违和感。
同样的感受也存在于民族乐器的使用当中。《后疫》中的民族乐器并不构成传统意义上的旋律或者乐句。偶尔出现的民乐声响,也更像是仙宫中若有若无的声音,勾画出的是另一种不属于尘世的氛围。在这个意义上,民族乐器和氛围电子合成器共同构成了这支曲子的主要基调,代表着窦唯一种超脱于世的观察视角。
不时穿插于这些背景音乐中的人生采样反而被衬托成了上述氛围的背景声。事实上,这些人声采样插入前后,都被刻意植入了一些电子音效,让他们显得像是来自于信号不佳的收音机或者电视。第一个在乐曲中出现的人声采样,一段关于德国总理默克尔对于疫情处置方式的新闻播报,就是在这样的编排下出现的,成为一段偶尔闯入收音机并被播放出来的声音。甚至,如果不仔细去听的话,这段声音都不能听得太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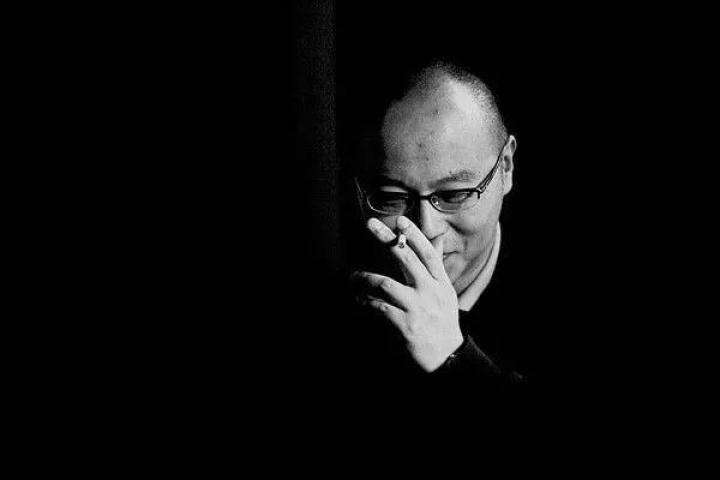
如今大众很少关注窦唯的作品,对他的记忆仍停留在那些花边新闻之上
这或许才是窦唯在编排人声采样时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后疫》中,人声采样的组织似乎并无明确的主题,而是随机的。来自于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声音被错落地安排其中,既没有疫情发展的时间顺序,也没有事件组织的逻辑顺序可言。从这些声音中,人们无法获取任何关于疫情的知识和洞见。窦唯所选取的这些声音并不是希望人们去听清,而是将他们视为一种背景音之下的底噪。
人声即噪音,也正是窦唯在过去很多年中所坚持的一个创作原则。2008 年,窦唯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访时曾说,从 2000 年开始,他就已经意识到语言的表达是无用的。在谈及自己的即兴演唱时,窦唯说:“我发音有音的成分,跟我这个乐声融合在一起,合情合理。来的人不是要听我表达什么思想,这些东西时下来讲近乎扯淡。都后殖民了你还表达什么?我觉得歌词已经完全没有意义了,完全是模式化的东西,那就免了吧。”
音乐,在窦唯看来,更能表达情绪、状态、以及想法。从 2006 年以后,窦唯的创作中就很少再出现完整的歌词了。他的很多即兴演唱也多用语气词这种传递态度,多过于传递内容的方式。他敌视人声的态度,表现在《后疫》当中,正是这样一种无组织的人声采样运用——将各种人声拼凑再一起,但却无法呈现任何意义,从而揭示出人类语言的无力和虚浮。
虚假的人声噪音,以及电子合成器和民乐创造出的氛围,或许代表了窦唯这样的态度:他试图站在事物之外,用旁观者的视角来看待过去几个月发生的、占据了人们几乎所有注意力的疫情一事。窦唯并没有加入人们对于疫情探讨的意思。《后疫》没有试图回应疫情带来的各种问题。疫情之于他,更像是偶然闯入他个人空间的杂音。

过多的关注和无界,或许是窦唯日渐走向封闭的原因之一
然而,杂音也同样影响到了窦唯。乐曲推进的过程中,人声采样逐渐与电子合成器和民乐构成了一种对抗关系。人声变得更加清晰,音量也逐渐增大,不同采样间切换的节奏也变得更快。这似乎暗示了变化,窦唯试图维持自己的超脱态度,但他自己作为人类的一份子,也无可避免地受到了人声杂音的干扰。合成器和民乐创造的冷寂氛围也出现了波动,笛子的声音开始高昂起来,变得不安而又杂乱。
《后疫》的最后两分钟处,突然出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声采样。它不再是之前大量运用的冷静的新闻播报,而是一个苍老的女声,语速极快地、激动地在控诉、辱骂、或者是在指责一些什么东西。她的声音不断放大,直至成为乐曲中唯一的焦点。最终整首曲子在她的一个感叹号中骤然而止。
结尾段落的愤怒、噪杂来得极快,又猝不及防,终于打破了先前营造出的冷漠、疏离的氛围。窦唯最终还是没有回避整个疫情带来的冲击。也正是在这个段落中,他似乎打破了自己一直所坚持的一种态度,达成了与人们的共情。
但这种共情与他对于语言的摒弃并不矛盾。最后的这段女声并没有使用汉语——大部分窦唯听众都能够识别出来的语言。听众只能纯粹从语气上去判断情绪。而这种方式正是窦唯所推崇的,用人声中的发音,去匹配音乐的乐声。这最后的段落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在情绪极尽激烈的时候,人声失去了传统意义上的表意作用,成为了音乐,而只有人声成为音乐,才能够起到人与人之间表达的作用。
在这个意义上,《后疫》仍然是一张窦唯展现自己个人音乐风格以及个人状态的作品。与他以往的作品一样,他的创作素材始终是个人生活的小世界,而不是具有广泛人文关怀的大世界。他会受到外界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真正关心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