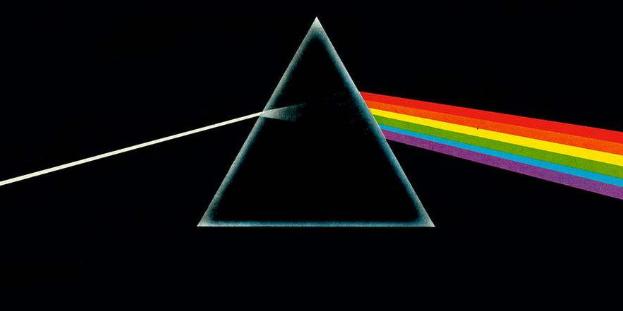
“他从内到外都浸润着那个时代的精神,无论是叛逆还是虚无。”
要概括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太难了。失控、大胆、狂妄、不羁、避孕药、超短裙、性解放、黑人民权运动等等,都是那个时代的关键词。那个时代的文学也是斑驳且忠诚的,1951年,塞林格用《麦田守望者》最早表现了那一届年轻人的苦闷困惑以及忠于自我的生存方式。之后的二十年,美国青年文化和文学沿着塞林格预示的道路一步步发展,经过金斯堡、克鲁亚克等“垮掉一代”的自娱自乐、自悲自悯,到海勒、品钦等“黑色幽默”作家的悲观、虚无以及对社会的批判和拒绝,到60年代末,美国青年已经完成了对时代和人生的反思,由激进转向反讽、虚无。
和塞林格一样,托马斯·品钦也非常擅长捕捉时代之下的精神状态。他从内到外都浸润着那个时代的精神,无论是叛逆还是虚无。在那部让人眼花缭乱的后现代主义巨著《万有引力之虹》中,他从被历史所抛弃的人的视角,从 V-2 型火箭与主人公的关系这个很小的切口出发,讲述了二战后期的大历史,但又好像有意与真实历史相对抗,各种隐喻、荒诞情节交错,一座宏伟的迷宫诞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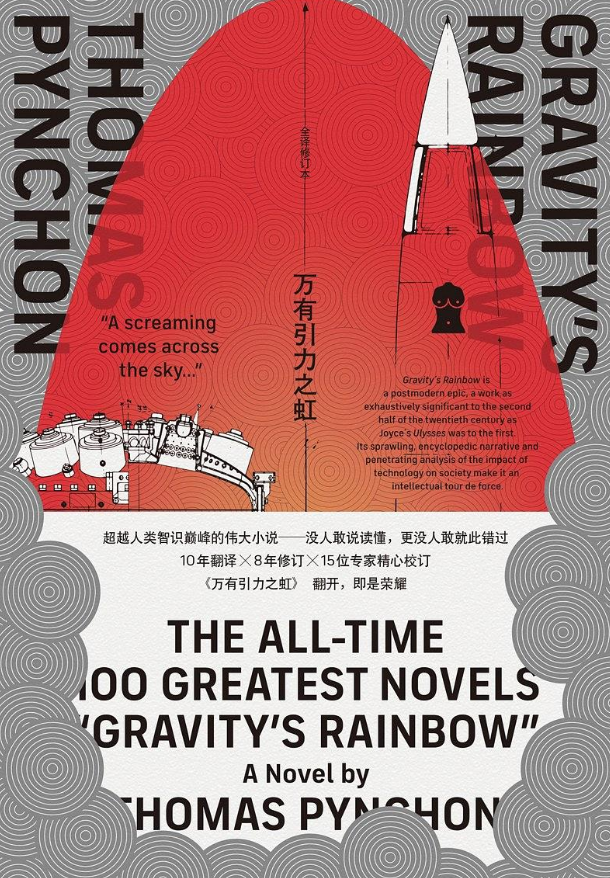
托马斯·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是一部长达九百页的小说,全书包罗万象,以二次大战为基本情节,但又穿插了无数杂乱的片断(诸如导弹技术与性变态),在文体上也是虚构叙述、随笔札记、议论评说的混合体。此为译林出版社将于本月出版的全译修订本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英美文学博士但汉松是品钦的“头号粉丝”,曾经亲自翻译过品钦的多部作品,比如《性本恶》、《慢慢学》等,他曾坦言,“品钦的小说,简直就是译者的关塔那摩、阿布格莱布……超级长句并非品钦的独门绝学,但他那种内旋的句法结构却是翻译上罕有的烫手山芋。”再加上隐藏于词句背后丰富又高深莫测的背景知识(迈克尔·夏邦曾在《月光狂想曲》中写道,在加州大学欧文分校修读迈克·克拉克的现代小说研讨班时读过《万有引力之虹》,对V-2火箭的大部分了解都是来自这本书),统计学,心理学,物理学,火箭弹道学……对译者来说,这样的挑战是可以想见的。
村上春树曾经开玩笑说,“如果我去翻译后现代作家,比如唐·德里罗、约翰·巴思,或者托马斯·品钦,那一定会撞车。”这自然不是一本好翻译的书,在《万有引力之虹》此前的译本中,译者张文宇收到的批评声不少。2016年底,受出版社委托,但汉松带领一批译者,无偿为本书进行校对。在漫长的校对过程中,他也逐渐体会到张文宇的不易。
“仅仅翻开,就是值得炫耀的事。”但汉松认为这句宣传语过于夸张了一些,仅仅翻开,不值得炫耀。在文学式微的当下,仍有人愿意付出所有时间和心血,将魔山一般的“天书”一点点砸开,碾碎,串联成跳动的汉字符,这就不仅仅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了。

很少有人见过品钦的“真面目”。这位出生于1937年的美国小说家善于“隐身”,曾于美国海军服役两年,1957年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后在波音公司担任技术作家。1960年起开始着手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V.》,其作品主要包括长篇小说《V.》(1963年)、《拍卖第四十九批》(1966年)、《万有引力之虹》(1973年)、《葡萄园》(1990年)、《梅森和迪克逊》(1997年)、《抵抗白昼》(2006年)、《性本恶》(2009年)、《尖峰时代》(2013年)及短篇小说集《慢慢学》(1984年),曾获得福克纳文学奖 、美国国家图书奖等多个奖项
修订版《万有引力之虹》本月即将上架,为了了解校译背后的故事,《全历史》对但汉松进行了采访,以下是采访实录:
“临危受命”的校对工作组
全历史:看到那天您的微博写了关于即将上架的《万有引力之虹》修订本背后的故事,您提到说译者张文宇当时为了翻译这本书做出了巨大牺牲,请问具体是什么样的牺牲?
但汉松:我们最好不要谈论译者的私事,但其实你可以宏观地想象一下:翻译这样一本书,需要一位大学老师多少时间和心血的投入。然后我们再想想,这里的机会成本问题。译者花在翻译上的时间,本可以去写论文、申请课题、赚外快,而在现在的学科评价体系中,翻译的分量是极低的,译者所获得的的酬劳也是和付出的辛苦不成比例的。
全历史:您后来“临危受命”组建的校对工作组,平时的工作模式是什么样的?
但汉松:这是一个比较自由松散的工作组。我们主要是建立了微信群,由我将译稿和原文做了对齐处理后平均分发给组员,因为中途有人退出,所以我自己做的部分更多一些。我也搜集了一些关于《万有引力之虹》的参考资料,主要是国外出的导读、注释和论文等等,也共享到小组里让大家参考。
全历史:校对过程中你们遇到了哪些具体困难?
但汉松:我想最大的问题还是理解。品钦的风格主要是两个极端,一种是各学科知识的广泛加载,而且不是那种浅尝辄止的简单名词征用,而是涉及到各个学科的具体原理,如果不深入了解其细节就很难识破他的科学梗。比如我在校对时涉及到降神会的场景,这个超自然的民间活动有点像碟仙,但里面分工明确,讲究甚多。光知道降神会是什么还不够,还需要找到资料知道其具体的操作细节,有了这个背景才能读懂品钦。很多时候我们看不懂,其实是自己缺乏这一块知识的储备。校对时,我们主要是利用这些年网络资料的极大丰盛来解决这些当初译本上的理解问题。如果对一个词或句子理解上是错误的,那么翻译得再行云流水也是白搭(而中文读者往往容易被译文的行云流水所欺骗)。品钦还有一个极端,就是他有时候会非常抒情,句子无比缠绕,各种文学意象堆叠。这是文学风格的问题,我们校对时一般不干涉张文宇的原译,尊重他的翻译风格和操作原则。
全历史:您还提到说,当您自己开始着手校对之后,才意识到很多时候读不懂是读者自己的问题,并不是张文宇译得不好,能不能举例说说文本里面有哪些地方是您觉得原译者处理得很巧妙的?
但汉松:这样的地方很多,因为我们校对并不针对其译入语的对齐转换,译者对于品钦的长句翻译尤其精彩,甚至小说中一些歌词的翻译也很到位,说明张文宇本身的中文功底是非常强的。
“在我看来,他就是20世纪最好的美国小说家”
全历史:像这个宣传语说的,仅仅翻开就是值得炫耀的事情,但我想可能最后能真正读完的人寥寥无几,所以在您看来,我们读品钦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包括品钦的现代意义,和您作为学者研究他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但汉松:宣传语不是我写的,我认为仅仅翻开不值得炫耀,读完或者起码大致读完,才算是可以吹吹牛的资本。品钦的意义当然如何夸大都不为过,他在我看来就是20世纪最好的美国小说家,我甚至不认为需要“之一”。品钦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过70年代流行的后现代主义文学那个风潮本身,他拒绝任何简单的标签化。品钦让我震撼地是对于美国历史乃至整个西方近现代历史的整体性把握,他能够以真正的渊博和现代主义文学最好的那种文学感受力,将我们所处的时代写入小说里。他符合我对于“伟大美国小说”的全部期待。对于《万有引力之虹》,我建议大家不要正襟危坐去读,我在亚马逊上看一个读者的评论,他说自己花了几个月读这本小说,然后从头笑到尾。其实品钦的书固然是皇皇巨著,但却又充满了阅读的谐趣,《万有引力之虹》可以把每一部分当成若干个vignette(片段)来读,不要有一下子吃掉整本书的压力,不要用读《战争与和平》的那种习惯去读它。眩晕是阅读它的基本体验,我们不要刻意要求自己立刻从整体上把握它。可以化整为零,那一个个的片段本身就是独立的文学宝石。
全历史:您认为在您的研读经历中,还有哪些作家可以和品钦相媲美?
但汉松:我认为美国当代文学是一个宝库,品钦、德里罗、罗斯、麦卡锡这样的白人男性大作家固然值得我们一读再读,很多女性作家、少数族裔作家也很不错,比如安妮·普鲁(Annie Proulx)和格洛里亚·内勒 (Gloria Naylor)就是我最近很喜欢的。文学的可能性是无穷无尽的,品钦的百科全书式后现代写作是其中一种。

安妮·普鲁
全历史:说到美国当代文学,您有没有觉得现在也有一些“步入式微”?时常被人说起的还是过去那些经典作家,虽然前几年Bob Dylan刚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但很多人觉得那都不算“正儿八经”的作家,像品钦这样百科全书式的作家已经几乎没有了......
但汉松:应该说美国30年代是一个大作家扎堆投胎的十年,他们这批人在60-70年代步入文坛,然后成为今日美国文坛的殿堂人物,他们有些还在世,比如德里罗、麦卡锡和品钦,有些已经离场,比如刚去世的罗斯和托尼莫里森。但从创作的活跃度来说,我认为美国依然是最具活力和多样性的国别文学,美国依然有世界最大规模的作家培养机制(如很多大小的创意写作班),也依然还有最大的严肃文学的读者群和研究队伍。诺奖只是一个指标物,不能由此断定美国文学的欲振乏力。当然,我的确也认为30年代出生的那批作家带来的黄金时代可能远去了,作家培训班体制也很难批量生产出大作家,同时图书市场讲究族裔和性别的多元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和以前那种正统的西方现代主义传承下来的美国当代文学有所不同,可能更多的新一代作家格局较小,缺乏像大卫·福斯特·华莱士这种敢写《无尽的玩笑》这类大小说的兴趣或能力。这或许是西方文学的普遍现象,但我依然相信会有伟大的作家和作品横空出世。
全历史:品钦据说还是纳博科夫的学生,有人说他们都是"黑色幽默"的代表,但实际上差别还挺大的。
但汉松:品钦和纳博科夫虽然都被归入后现代文学,但两人风格的确很不一样。他们不是一代人,文学趣味差别也很大。虽然在康奈尔大学有过交集,但其实品钦似乎对纳博科夫印象一般,纳博科夫更是不记得品钦在自己班上。
翻译,是一个作家和另一个作家最深沉的耳鬓厮磨
全历史:您怎么看待文学作品中的翻译腔?有的中文作者在语言上会刻意模仿一种翻译腔的语调,您认为在实际写作中,作家是应该避免这种情况出现还是就顺着自己的喜好?
但汉松:翻译腔没什么不好,这不是在开拓当代汉语的可能性吗?现在很多人一说到地道的汉语,就以为是细碎的短句,认为那些复杂的长句是翻译腔,其实是一种偏见。不要天然地认为翻译腔就是一种原罪和劣等的汉语。村上春树是一个例子,他的日语语感其实受到英语的影响,因为他从小就是读美国小说长大的,他的文学母体不是纯正的日本文学。
全历史:有人说翻译就是在为他人做嫁衣,但其实对文学翻译来说,直译其实是很让译者为难的,因为对于不同语系来说,比如中英文,很多英文里说得通的表达,要是直译的话,意思就完全变了,所以这时候只能靠意译。我记得您之前在《性本恶》的译后记中谈过,译者一旦“忠实”于品钦原本就“不通顺”的原文,那么译文就肯定无以“达雅”;可如果考虑到可读性让品钦朗朗上口,那就几乎一定是译者越俎代庖,甚至谋权篡位了。所以您作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是怎么平衡“直译“与”意译“的?
但汉松:我觉得没有一般性的操作手册,需要译者在每一句、每一个词上具体斟酌,甚至同一个译者在不同时期对语言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我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忠实首先是第一位的。如果对原文意思的理解都是拧巴的,译文再生动漂亮也是白扯。对于品钦这样的作者来说,忠实更加是第一位的,不能为了照顾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和语感,就把品钦的文风做降调或者改良处理。在文学中,形式有时候就是内容本身,品钦希望读者在“不通顺”、“缠绕”的阅读中慢下来。中国读者读外国文学译本太容易一目十行了,这有点买椟还珠了。
全历史:其实很多译者本身也是很出色的写作者,既然如此,您认为为什么还是会有这么多好作家愿意去做这件“嫁衣“?
但汉松:是的,很多大作家自己也做翻译,譬如村上春树也是美国文学的译者。翻译,是一个作家和另一个作家最深沉的耳鬓厮磨。我认为,它属于一种最高级的“粉圈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