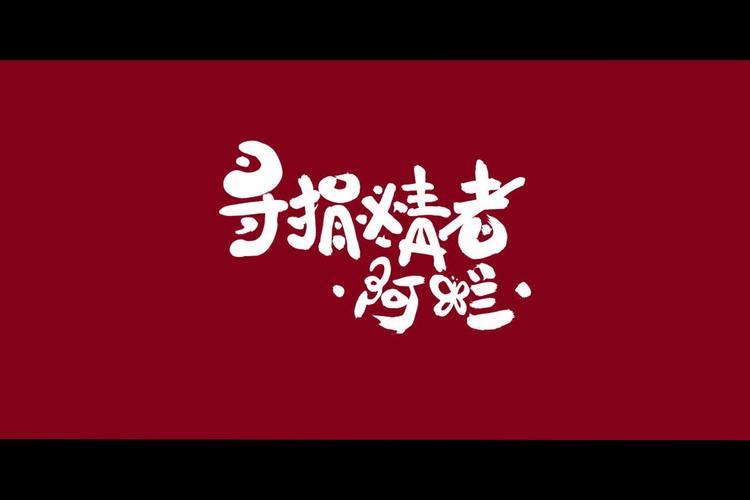
2019 年 1 月 22 日,她在自媒体号上发布“征捐精者”视频,还曾在网上自我调侃,“我不想结婚了,但想和你生猪宝宝。”随后,她像面试一样进行筛选应征者。
图文:朱玲玉
文字编辑:王晓

阿烂,90后自由职业者,青年画家/行为艺术家/网络编辑/公益人士。现居北京。
认识阿烂是在2017年。印象中,当时的她是个古灵精怪的姑娘,一个天马行空的艺术家。
也就是在那一年,阿烂搞起了网络征婚,一连搞了三次。她给自己安了个大龄单身文艺女青年的人设。接着,她又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全国流浪”计划。从来没学过绘画的她,曾用117天绘制了170张墨水画。在她的画中,有人看到了童真,有人说她有艺术创造力,有的人认为只是涂鸦。于是,她众筹办了画展,甚至把画展搬到了芬兰。
2018年,阿烂加入一个名为多元家庭网络的民间公益平台,致力于推动女性生育权,倡导多元家庭的理念。她又多了一个身份——女权主义者。
2019 年 1 月 22 日,她在自媒体号上发布“征捐精者”视频。之后,她像面试一样进行筛选应征者,曾在网上自我调侃,“我不想结婚了, 但想和你生猪宝宝。”
这时候网上的质疑声出现了,有人把这次举动当成又一次的行为艺术,有人批评她把男性当成生育工具,也有人表达了对女权的支持。面对“把男性生育工具化”的质疑,阿烂表态:“这也没毛病,如果是两厢情愿,为什么不可以?”

阿烂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她是印象中那个古灵精怪的女孩吗?又或者只是一个旗帜鲜明的女权主义者?网上呈现的她和现实中的她,到底是什么关系?我有些好奇了。更让我意外的是,2019年7月,从她的朋友圈得知,她已经征精成功并开始受孕。
2020年4月初,我联系了阿烂,此时,她的孕期已满36周,即将临产。我提出想要看看她的生活,听听她的故事。阿烂同意了。于是,我背着设备住进了阿烂家。
在之后挑选图片的过程中,我有意选取了部分她自己po在网上和朋友圈的照片,以及我在现场抓怕的生活照。我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对比的编排,可以完整地呈现她的面貌。最后,我还搭了一个简易的影棚,为她拍了三张不同形式的肖像,表现我对她三个面向的观看维度和同一个社会面孔在虚拟、现实之间的不同解读。

左图:2018年,阿烂的写真照。(供图/阿烂)
右图:2020年4月晚,孕晚期的阿烂,脸上浮现几分困意。身子的沉重感让她开始期待“卸货”。
互联网实验第一步:征婚
2017年,阿烂满25周岁,也就是中国婚姻文化中所谓的“适婚黄金年龄”。虽然父母没给她施压,但毕竟生活在中国式催婚的语境下,她也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一年半里,她先后三次在网上征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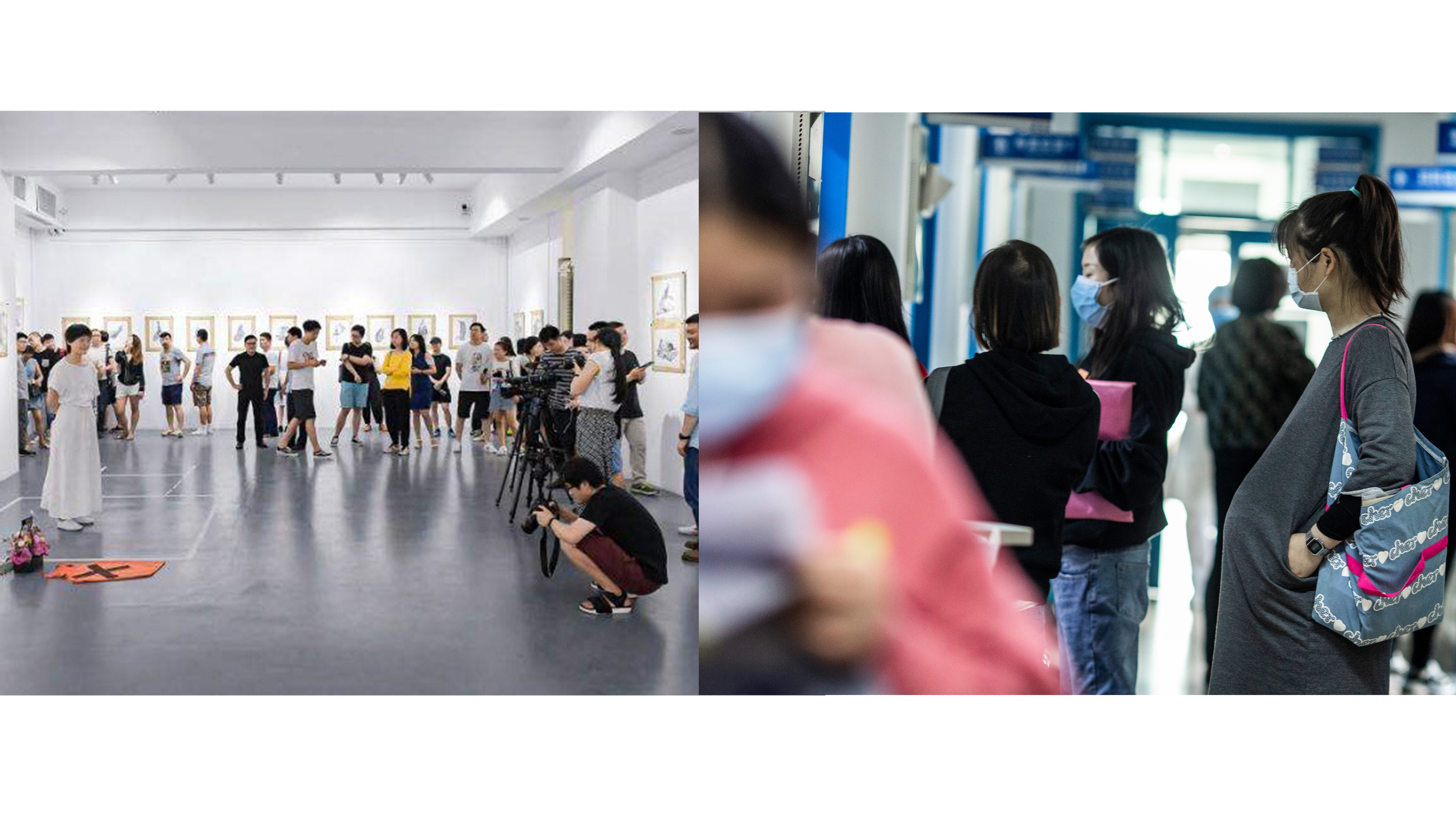
左图:阿烂在798凤凰含章艺术中心举办个人画展。“白天是殡葬师,晚上是插画家”的身份反差,让她开始被自媒体平台关注。(供图/阿烂)
右图:阿烂怀孕九个月,在产科门诊待检。
征婚启事中,阿烂写,“为什么要结婚?为什么不结婚会有这么大压力?为什么女孩的年龄是一个问题?为什么一定要找到一个男人?我实在无法被动接受这一切,面对结婚这个议题,我选择主动出击。”
直到现在,阿烂认为自己始终不认可“必须要结婚”这个概念。至于征婚行为,是她的一次互联网行为实验,“我要在网络上塑造一个大龄单身未婚女青年的形象,最后,我成功了。”自征婚后,阿烂便发现她已成功地让大家以为自己是多么“恨嫁”。每次与人见面都会被问到“你找得咋样了?”“还没有找到吗?”从网络中应征来找她的人也有几十个不等,不乏有来看热闹的,也有表示支持的同性。

左图:阿烂在个人画展上表演“任你进入”行为艺术。在2x2的方型区域内,不使用口头语言,围观者可以使用法律发内内的任何形式与她进行互动。阿烂试图通过这个行为艺术探讨人与人关系的界限。(供图/阿烂)
右图:2020年4月3日,阿烂独自在医院做例行产检。医生告诉她肚子里的宝宝有5斤5两重。她有些担心,“是不是平时饮食没特别补,所以胎儿长得小?”旁人安慰,“个小,你生得不用那么辛苦。”
在阿烂对这场行为实验的设想里,征婚启事只是第一步。如果通过这种方式,真的找到这么个人结婚了,再告诉大家这是一场实验。如果没征集到结婚对象,她可以接受这个虚构来的结果,“但也许我真的找到合适的人结婚,对方是从这个虚构的实验中参与进来的,我也接受这段可能真实发生的缘分。”

左图:阿烂书桌上的两张便签,左边标注了“出生证明”、“户口薄”、“法律条例”的字样,右边写着“与你无关,与自己有关”、“少女阿烂成为母亲”。
右图:孕晚期,阿烂的手和脚都出现水肿。
当被问及为何要做这场实验的时候,阿烂不假思索地回答,“在网络里我们很难知道一个人到底是怎样的,因为平时我们po出来的照片总是好的一面,真实生活可能一团糟。我们在社团网络里呈现出的某一部分,有可能是虚构出来的,又有可能是我们期待的生活景象。不管是虚构还是真实,它都代表了心里的一部分。”
在阿烂的画作中,也常出现一些被抹去脸部五官或者无脸的人物。在她看来,一个被互联网消费的人,可以不需要脸。我们生活在信息海啸里,真实的内核被隐匿,被po出来的一面所曲解的现实另一面, 其实就是内心的缺失。

左图:2019 年,阿烂正在指导摄影师拍摄征婚视频。(供图/阿烂)
右图:2020 年 4 月 1 日,阿烂在菜市场买菜。菜贩子告诉她,孕妇多吃大鹅蛋,可以预防胎儿黄疸。8 元一只,她扫码买了两只。
第二步:寻精计划
在征婚的过程当中,阿烂慢慢发现自己对结婚和征婚行为实验都没了兴趣。“我意识到自己更直接的需求并不是结婚,而是生育。女人最佳生育年龄是 24-29 岁,我已经 27 岁了,当时我就给了自己一个年限,30 岁之前完成生育。”
国内精子库不对非婚女性开放,有朋友便建议她去国外买精子,但是阿烂并不具备这个经济实力。为了扩大征集范围,她找到一位叫阿坤的摄影师朋友,为她拍摄一个“征捐精者”短视频,在网上发布。

左图:阿烂孕前在景区留影。(供图/阿烂)
右图:阿烂在厨房炒菜。养胎期间,基本上她都是自己买菜、做饭、洗衣洗碗,下楼拿快递。
相对于征婚,征精一举在围观者眼里以更谨慎的态度对待,通过征集帖来联系她的人只有十几个。聊下来之后,阿烂发现真正有和她一起合作生育的意愿者,筛选下来只剩下 3 个。随后,她 便像“面试”一样,相继和他们进行线下接触,“像筛选精子库一样,考虑基因质量、 学历、经济能力、外形条件等等综合因素”。
第一位志愿者,是个20岁的北京男生,国外留学回来。他对阿烂表示了“不想结婚但想生孩子的”的决心,并提出自己的合作条件——保险、抚养费、相应的陪伴,但是户口不能上在他名下,必须隐瞒家人。阿烂觉得对方太年轻,不成熟,对育儿又一窍不通,便不再与之见面。

左图:2018年,阿烂“流浪一年”行走计划在山顶留影。(供图/阿烂)
右图:2020 年,阿烂在出租屋里为母亲节策划“单身妈妈”视频制作文案。她依然坚持为多元家庭网络平台撰稿。
第二位志愿者,是个已婚的中年男性,名校毕业,多金,长得也还不错。他和妻子生了两个孩子,还曾为一对拉拉捐精。对方提出,给她和孩子400万的抚育基金。“单纯从合作角度来看,他的条件很好。”但阿烂还是拒绝了,她觉得对方把生孩子当成了嗜好,自信自己基因优秀可以遍地撒种。
第三位志愿者是个30 岁左右的单身男同性恋。经济实力、长相、身材都符合阿烂的审美。可是两人只见了四五次,对方手都没和她牵过,他就向阿烂提出一起合资买房,作为将来对孩子的支持。但行为举止上,则表现出对她的淡漠。最终让阿烂放弃了与他合作的念头。
这让阿烂意识到,这些志愿者并不能和自己在尊重和平等的关系前提下,实现合作生育的意愿。而她想要的并不再是一颗精子,而是给孩子找一个爸爸,合作双方还是需要感情基础。

左图:2017年,阿烂“流浪一年”行走计划,在海边留影。(供图/阿烂)
右图:2020年4月2日,阿烂在厨房切菜。
出于这个因素的考虑,阿烂最终挑中了摄影师阿坤。阿坤对她一直很好,性格温和、腼腆,让她笃定对方“会是一个好爸爸”。
她和阿坤在北京丰台区合租了一个两居室,每月租金3500元,开始尝试受孕。2019年9月,试纸上的两条红线,让阿烂喜出望外。
当理想撞见现实

左图:2017 年,阿烂“流浪一年”计划途中留影。(供图/阿烂)
右图:2020 年 4 月,阿烂在妇产科做胎心监测。医生说胎儿活动次数不多。阿烂解释,上午他都不怎么动弹。接着,她用手拍拍肚皮,胎儿跟着声音节奏,多动了几下。
确诊怀孕后,阿烂打电话告诉母亲。母亲说:“这不是你一直想要的吗?恭喜你。”几个月后,母亲才在媒体报道中得知阿烂的“征精计划”,她来电话提及此事,阿烂赶紧岔开了话题。在双方父亲眼里,早已认定他们是夫妻。

左图:2019年,阿烂旅途留影。(供图/阿烂)
右图:2019年4月3日上午,阿烂在医院走廊吃巧克力,以补充体力。医院的电梯维修因为疫情延迟,她只能在妇产科、检验科、挂号窗口、B超室间来回折返,上下楼都带喘。
作为自由职业者,阿烂收入不高,阿坤则是一名普通工薪阶层。但阿烂不担心经济上的困境,“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孩子都能养大”。她觉得自己具有相应的社会支持条件,父母会给予相应的经济支持,朋友也可以帮忙。她计划在抚育阶段,阿坤负责赚钱,自己全职带娃,让家里的老人来帮衬。
“我是通过一颗精子来找到孩子的爸。这个精子的提供者,这个爸爸将具有怎么样的品质,才是更重要的。我在乎他作为爸爸怎么样,而不是他跟我关系怎么样。”阿烂坦言自己曾假想,“有一天如果我不能照顾这个孩子,出于对孩子的爱,他也一定会把孩子照顾好。”

左图:2019年,阿烂孕前朋友圈自拍照。(供图/阿烂)
右图:2020年4月2日晚,阿坤为阿烂端来洗脚水泡脚。
这从某种程度上和阿烂倡导的多元化家庭模式相契合。这两年,她和多元家庭网络平台在多方资源的协作下,为“国内首个单身女性冻卵案”、“单身母亲生育保险案”推波助澜,还多次向人大提案呼吁国内精子库放开单身女性冻卵权利。目前中国单身女性生育群体面临两个极端境遇,或是在经济实力雄厚的情况下出国买精试管,避开国内生育政策的天平倾斜;又或是不具备相应经济承受能力的情况下,生育后面临就业困难、单亲抚养压力、政策不平等对待、社会多方隐形歧视等多重困境。
中国单身母亲群体的现实境况,也注定成为阿烂这场行为实验无法贯彻下去的暗礁。在阿烂寻精的过程中,也显露过几分“挣扎”和矛盾。
阿烂认为,从社会层面,除了普遍双亲生育的家庭结构,单身生育也是一种形式,她所实践的也是一种,有更多的可能性总是不被社会看见。这场行为实验只关乎个人在家庭结构的探索和实践, 她的生育实践全为了满足个人需求,并不会为了推动而推动。

左图:阿烂“流浪一年”行走计划在海边留影。(供图/阿烂)
右图:阿烂独自在妇产科门诊测量血压。
谈及她阿坤的关系,她认为他们更像是生育的合作伙伴和生活伴侣,不是浪漫爱的那种,也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夫妻。
“中国的婚育文化里其实不存在真正的浪漫爱,它本身就不是我的计划里面的必需品。有的话,是我的幸运,不是我不也强求。”目前,阿烂和阿坤各睡各的房间,连烧水壶都是各用各的,平常夫妻里那种行为习惯的互相渗透并未发生在他们之间,她也希望保持这种空间和心理上的相对独立。

左图:阿烂自拍孕照。(供图/阿烂)
右图:阿烂在镜中观察自己的妊娠纹。进入孕晚期后,她的体重从120斤飙到170斤。
看起来,这场寻精计划从一杆旗帜鲜明的行为作品,转变成了一场普通意义上的征婚相亲。
但阿烂认为,“从征婚、征精到抚育,都还在这个互联网实验的过程里走着,是完全符合我期待的”。这场实验的意义,只是实现她个人生娃的需求,等到孩子出生,实验便走向真正的实践了,就是“我如何去体验这个抚育过程”。她希望能在抚育阶段延续自己的独立和自由空间,这是这个实验探索的最终理想状态。

左图:阿烂朋友圈孕照。(供图/阿烂)
右图:阿烂摘下口罩,靠在小卖部门口晒太阳。
在和心理咨询师谈及为何不领证的原因时,阿烂追根溯源,可能还是归因于原生家庭。她说母亲当年就是迫于家族催婚压力结的婚,婚后很后悔,直到她出生,重心才从婚姻关系转移到了孩子身上。这样的家庭关系虽然符合传统意义上的完整,但并未让阿烂的童年获得充分的陪伴。阿烂记得,她小时候经常一个人在家,翻书架上那些大人看的书,和自己玩游戏。

这也让阿烂意识到中国女性面对的婚育文化制约和困境一直是普遍的,她不想让自己成为为了结婚而结婚的群体之一。她认为,这场行为实验,出发点是出于对传统婚生程序的不认同,但“为了行政程序上的方便,也许会考虑领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