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老是有那样的感觉,哪怕只活一天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
前一阵美国人(因为保持社交距离而感到孤独)刚说自己成了爱德华·霍珀(隔离中的“美国式孤独”),最近英国人也发声了,We are all Mrs. Dalloway now(现在我们都成了达洛维夫人)。当出门都成了高风险活动,最平常不过的外出吃饭、购物似乎也成了“生死攸关”的大事,弗吉尼亚·伍尔夫名作《达洛维夫人》主人公克拉丽莎·达洛维夫人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人们共鸣:
达洛维夫人说她要自己去买花。
她看着一辆辆出租车,有了一种永恒的疏离感,她仿佛越走越远,孤身一人地,一直走到遥远的海边。她老是有那样的感觉,哪怕只活一天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
这世界刚经历过的那些事情令他们每一个人,令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泪如雨下。但他们有着泪水与悲痛,勇气与坚韧,绝对的正义感,如斯多葛教徒一般的忍耐力。

电影《达洛维夫人》
网友们的玩梗能力是惊人的。开头那句“达洛维夫人说她要自己去买花“已根据现实情境在推特上被篡改成多个版本:
达洛维夫人说她要自己给门把手消毒。
达洛维夫人说她要自己去买消毒剂。
达洛维夫人说她要自己做口罩。
达洛维夫人说她要自己去感染病毒。
实际上,这本书能引起共鸣并不奇怪。《达洛维夫人》的故事发生在1923年,距离导致5000万到1亿人死亡的那场瘟疫已经过去五年。克拉丽莎·达洛维(Clarissa Dalloway)是幸存者之一。书中有一个情节,达洛维的一个邻居看着她,发现她“自从生病后变得非常苍白”;二十多年来,在车来人往中或夜半醒来时,达洛维“都会确信人们会感觉到一种特别的宁静与肃穆,一种难以形容的停滞感,在大本钟敲响之前的焦虑感”,人们说那也许是因为她的心脏受到了流感的影响。
尽管1918年的流感从未被直接提及,但学者伊丽莎白·奥特卡(Elizabeth Outka)在她的新书《病毒现代主义:流感大流行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文学》(Viral Modernism: the Influenza and Interwar Literature)中认为,任何涉及有关当年流感的事物都会唤起人们对瘟疫的记忆。小说中,类似频繁响起的钟声,空气中溶解的铅圈等等,都相当微妙地将疫病召唤。对此,Outka在她的书中解释道,与瘟疫最相关的现象之一就是“不断为受害者敲响的丧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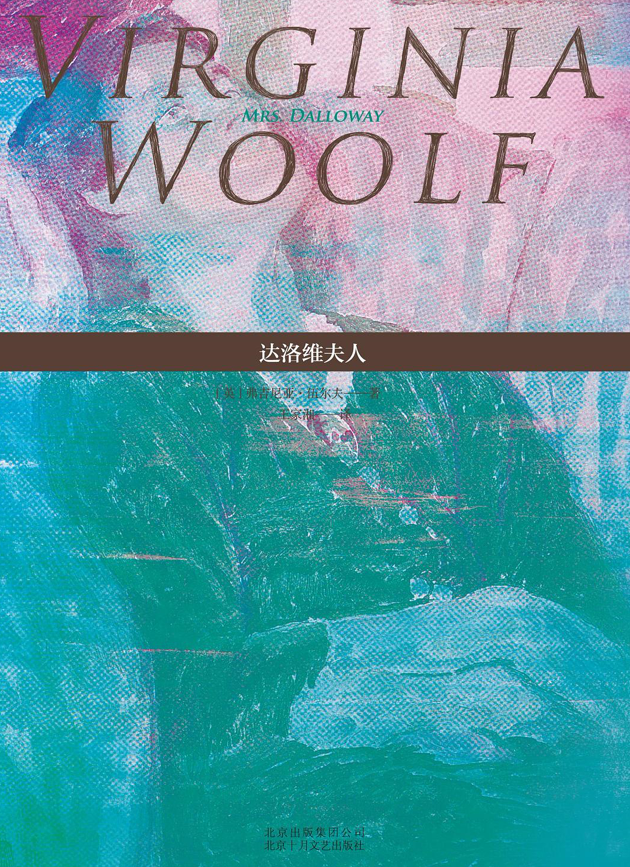
2015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达洛维夫人》
伍尔夫本人其实与瘟疫鏖战多年。1895年,她的母亲死于由流感引起的心力衰竭,这引发了她的第一次精神崩溃。在1916年到1925年之间,伍尔夫自己也得了六次重病,需要长时间卧床。流感影响了她的心脏功能,就像达洛维夫人的心脏一样。在这段时间里,她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1922年,为了防止感染,在医生乔治·萨维奇爵士(Sir George Savage)的建议下,她拔掉了三颗牙齿(乔治·萨维奇爵士是《达洛维夫人》中讨厌的威廉·布拉德肖爵士的原型)。
伍尔夫和其他人一样明白病毒对身体和社会的长期影响。但她也明白,不是每个人都能谈论它,也不是每个人都想听到它。“不然人们会认为,小说是专门讲流感的,”伍尔夫在她1926年的文章《论生病》中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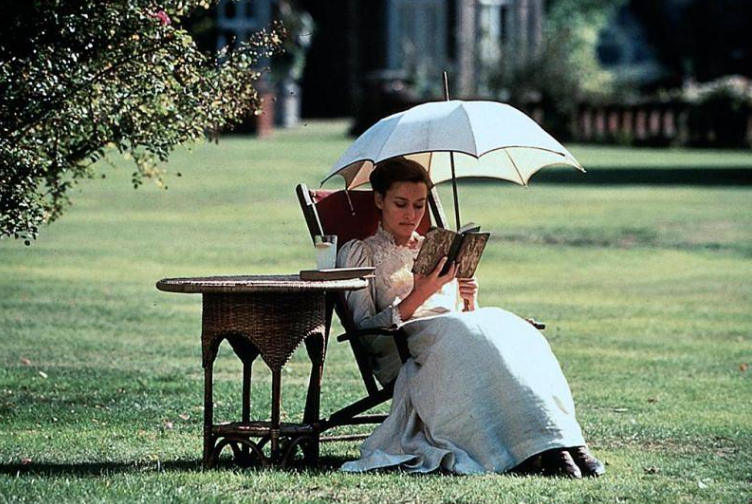
对于一次导致全球逾5%的人口死亡的灾难来说,1918年的瘟疫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远低于预期。一方面是因为它发生在1918年和1919年初,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数以百万计的亡灵没有像战争伤亡记录那样被载入历史,”Outka写道。即使在当时,关于这场流行病的新闻报道与跟战争有关的报道比起来也少得多。
Outka认为,虽然人们已经习惯于将战争死亡视为“英勇的牺牲”,但流行病“撕开了这层以牺牲为名的虚伪外表”。当时有一种普遍的态度是,战场上的死亡可以被视为英勇,但死于流感就成了一种耻辱。“对作家来说也是如此,写关于流感的文章可能会让人觉得不忠诚、不爱国,这是对重大事件的一种回避,因此很多作家只能偷偷写,很多反映流感的作品也上不了台面,就像一个贵族家庭里的“主仆之分”。
此外,战争和流感还有性别之分。1918年,男人女人都一样处于极度危险之中,居家变得和前线一样致命。Outka写道,使男人牺牲的战争成为了故事主角,而使男人和女人都死去的瘟疫却不能有姓名。

Virginia Woolf
实际上,与一战有关的情节和人物也出现在了《达洛维夫人》中,最引人注目的角色是老兵西普提莫斯·史密斯(Septimus Smith),他被幻觉折磨,并最终跳楼自杀。大多数评论家将塞普提莫斯视作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例子,他的故事也被当作是伍尔夫在暗指当时英国社会未能处理好因战争造成的大部分人的“心理后遗症”。但Outka认为,塞普提莫斯的症状,如谵妄、幻觉,也可能是由瘟疫造成的,大规模的瘟疫会“导致短期和长期的精神不稳定”。因此,塞普提莫斯极可能是遭受到战争和瘟疫的双重折磨。
在1918年那场瘟疫中,士兵的感染率极高。撇开字面上的种种缘由,塞普提莫斯的悲剧也正是达洛维夫人所遭受的“虚无的痛苦”:当达洛维夫人得知塞普提莫斯的死讯,然后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她的灾难——她的耻辱。”战争带来的灾难和疾病带来的耻辱在伍尔夫小说中是紧密相联的。

然而,把《达洛维夫人》看作是一部关于流感的小说能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分析主人公克拉丽莎·达洛维穿越这座城市的乐趣。对达洛维来说,伦敦被“神圣的活力”所激活,其密度和拥挤被视为生命力的标志,但也正是由此使得它在1918年“被吞没”。瘟疫暂时溶解了浮光跃金,也正是当前处于“非常时期”中城市的模样。
如今当人们置身于空空荡荡的街道时,又会重新怀念曾经的“生机勃勃”:“在或轻盈或沉重或艰难的步伐中,在咆哮与喧嚣中,在马车、汽车、大巴、货车和身前背后挂着广告牌摇摇晃晃蹒跚而行的人中,在铜管乐队中,在管风琴中,在欢庆声中,在叮当声中,在头顶上一架飞机发出的奇特而尖利的呼啸声中,有着她热爱的一切。”这是达洛维夫人的心声,也是现在所有英国人的心声。
参考来源:纽约客、《达洛维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