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实,不管在中国,还是在国外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离婚程序里,作为一种离婚障碍的“冷静期”,并不是个新鲜事物。
5月初,一名律师博主发布了一条短视频,在封面上用黄色字体打出标题:2020年以后想离婚比结婚还难。
“2020年的民法典草案规定了30天的离婚‘冷静期’和30天的离婚‘抉择期’。”这名博主在视频中声称。目前,这条视频在抖音的点击量接近两百万,评论数超过十二万,其他社交平台如豆瓣、知乎等,也出现相关的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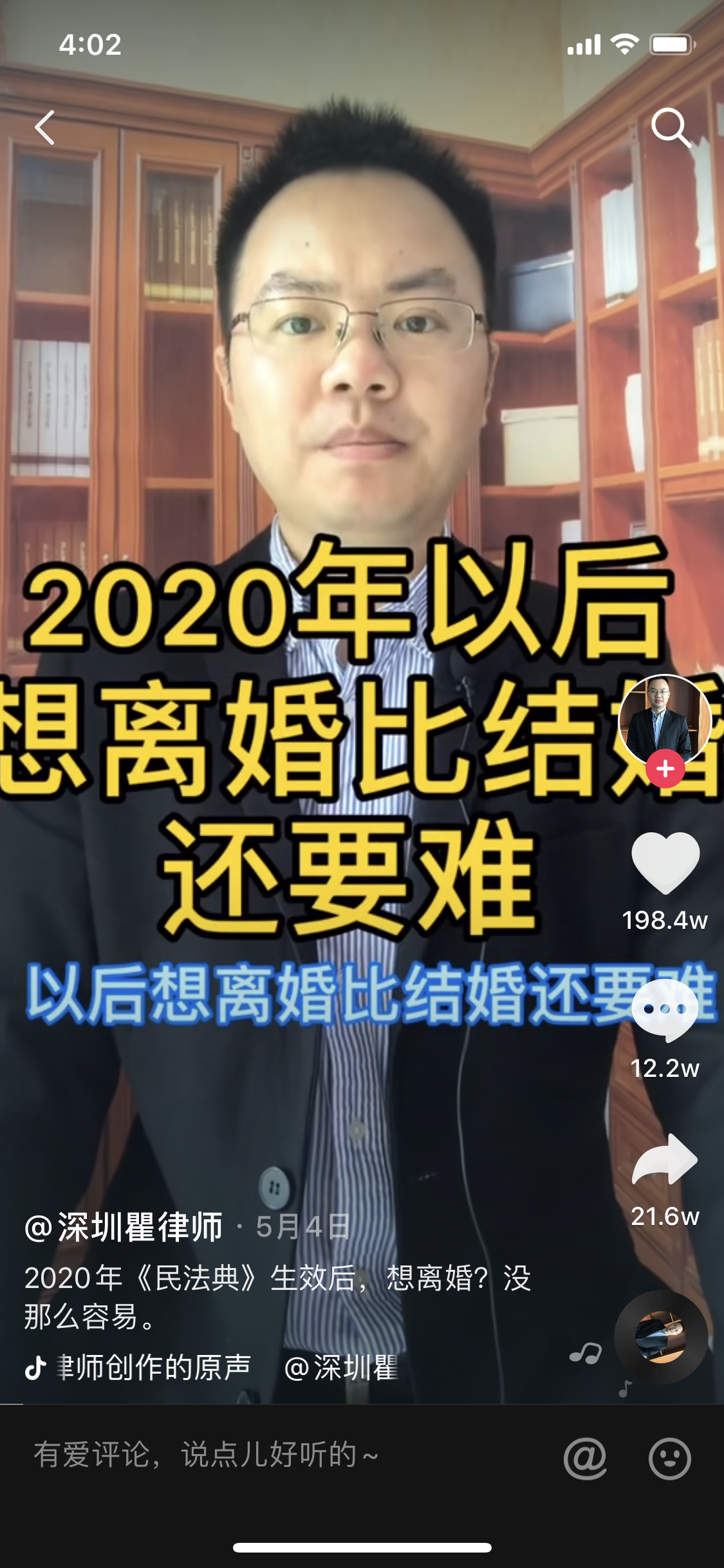
一名博主讲解民法典草案中关于离婚“冷静期”的规定
有人表示:“这样好,离婚不能太随便了。”
也有人说:“今日份恐婚。”
还有人说:“那结婚也该缓冲60天。”
其实,不管在中国,还是在国外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离婚程序里,作为一种离婚障碍的“冷静期”,并不是个新鲜事物。
存在多年的“冷静期”
关于所谓的“冷静期”和“抉择期”,在民法典草案中的完整表述是:
“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申请。前款规定期间届满三十日内,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未申请的,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
这个规定只针对协议离婚。2003年开始,中国的离婚率逐年攀升,每年都引起公众和学者的讨论。而在离婚制度设计方面,2003年也是一个节点——这一年颁布了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这一版的条例废除了此前作为离婚前置程序的审查制,旨在维护个体的私人权利与自由,避免公权力的过度干预私权利。

离婚登记审查虽然从条例中消失,不过“离婚需谨慎”的价值取向,在很多地方婚姻登记机关的实践中却延续下来。此次民法典所提出的“冷静期”,在实践中也存在多年。
2004年,上海市婚姻登记机关采取了发放“离婚告知书”的方式, 希望当事人能在“告知期间”内冷静下来并重新考虑是否终止双方的婚姻关系。此后,“离婚冷静期”陆续在各地都有过试水。
比如,2018年,四川安岳县民政局成立家事纠纷协同化解工作室,以“冲动式离婚群体”为对象,通过劝和、回访与发放《离婚冷静提示书》的方式,给当事人一段时间重新考虑。

还有的地方搞预约离婚登记制度,也相当于提供了一段时间的“冷静期”。 2013年,广东东阳市婚姻登记处推行离婚预约登记,凡办理离婚的夫妻,要预约满7天后才能办理正式离婚手续。从数据上来看,似乎确有遏制“冲动离婚”的效果。当年,东阳预约2549对,实际办理1061对,预约了离婚却没有办理的高达58%。同年,东阳市实际办理离婚人数同比下降了近15%。
而在诉讼离婚程序中,“冷静期”也存在于司法实践中。各地方法院秉持的精神是“完善家事审判,构建和谐家庭”。上海、四川、河南等省市都在基层法院试点过离婚冷静期。2018年最高法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意见(试行)》,提出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可以设置不超过 3 个月 的冷静期。
由此可见,被写进民法典草案的“冷静期”,虽然仅针对协议离婚的情况,也可能是首次将“冷静期”这一制度在中国以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
离婚,从来就很难
现代婚姻制度史上,离婚原本就比结婚难。
1969年以前,美国大多数州实施的是过错离婚,要解除婚姻关系,须向法庭证明离婚当事人有过错,导致 “不可挽回的婚姻失败”。加州是美国首个将无过错离婚合法化的州。此后,各州开始陆续进行离婚法改革。2010年,纽约州通过了新的离婚法案,成为美国最后一个采纳无过错离婚原则的联邦州。
西方社会其他国家的离婚法,大体也都经历了类似从过错主义向无过错主义转变的过程。在中国,1980年第二部《婚姻法》确立“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裁判离婚标准,也被视作无过错离婚原则确立的标志之一。
与这个转变同步发生的,是全球范围内离婚率总体呈现的增长趋势。不过,离婚依旧不容易。还是以美国为例,各州在离婚登记制度中,都通过设置离婚障碍来限制无过错离婚原则的滥用——离婚等待期就是其中一种。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是设立离婚等待期的重要考量。

电影《婚姻故事》,讲了一个离婚的故事
比如,俄克拉荷马州的《相互同意法》规定,在存在未成年子女时,夫妻不能单方面宣布离婚,除非夫妻一致决定离婚,要想单方面宣布离婚,必须等到子女成年以后。
纽约州的《纽约家庭关系法》也有类似规定:除非在一方遭受家庭暴力、囚禁或者精神病威胁的情况下,任何一方要离婚,都必须经过约一年的警告期,如果家庭中存在未成年子女,则还要延长一年。在这期间,夫妻双方将接受离婚指导和教育课程,让双方考虑婚姻是否还可持续。
再看看欧洲,也设置了各种离婚障碍。
法国的协议离婚,双方有十五天的考虑期。诉讼离婚程序中也有类似的设置:离婚当事人有最长8天的考虑期,然后由法官或调解员进行调解,如果调解无效,才正式开庭审理。
有的国家虽然没有明文规定“考虑期”,但却需要离婚双方分居。德国民法典规定离婚的唯一理由是“婚姻破裂”,而一定时间的分居,则是推定婚姻破裂的要件。“如规律共同生活关系不复存在并且已不能期待恢复共同生活关系时,判定婚姻破裂。”
很多时候,离婚障碍设置的出发点,也是为保护婚姻中弱势一方。1977年,韩国民法典设置了家庭法院法官确认离婚协议程序,夫妻双方须在法官面前陈述真实意愿,如果妻子表示无离婚意愿,则不批准离婚协议。2006年,韩国民法修正案中,增加了协议离婚里离婚咨询与强制实施“离婚熟虑期间”规定。
恐婚,也恐离婚

1969年之前,美国普遍施行过错离婚制度 图:《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第三季
美剧《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中,女主角从第一季开始就在办离婚,结果到第三季才终于离成。在法庭上,法官惊讶于男主Joel支持自己的妻子离婚,看不出两个人“有什么分开的必要”,直到Joel为了尽快走完程序、让法官有理由判离,不得不给往自己身上泼脏水,声称自己不止一次出轨,观众们才终于听到法官敲下的那声锤响:“批准离婚申请。”
麦瑟尔夫人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今天,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婚姻制度仍旧是不“鼓励”人们解除婚姻关系的。对离婚障碍的设置,一方面是为考虑离婚对家庭成员造成的影响(未成年子女、孕期妇女、全职家庭主妇等),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一种普遍的价值取向——人们认为家庭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也是个人价值实现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婚姻衰落”的担忧并不是近几十年的专利。史蒂芬妮·孔茨在《为爱成婚》中写道:“古希腊人对于妻子们日渐堕落的道德充满怨言。罗马人哀叹他们的高离婚率,还拿早前家庭稳定的时代与之对比。在美洲的欧洲殖民者,几乎从一下船就开始痛心于家庭的衰落和妇女儿童的难以管束了。”孔茨认为,不管在哪个年代,人们总是倾向于认为过去的婚姻比当下好。

不同文化下,人们对婚姻都抱有“完整”和“美满”的期待。许多天主教国家都曾禁止离婚, 或者在一度开禁之后又重新迫使政府发布新的禁令。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 ,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让离婚成为可能。巴西和阿根廷也属此列 , 它们相继在1977年和1986年解除离婚禁条 。
同样地,“离婚自由”也作为当代产生的价值的一部分,冲击着终身婚姻制。苏联曾经走得比较激进——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就可离婚。在中国,“冷静期”的设置和实践,也是争议重重。反对者认为,对于不同的离婚案件,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并不能正确反应当事人诉求。
并非人人都能从婚姻里收获幸福。王尔德也曾毒舌地说:“什么是离婚的主要原因?结婚。”今后,离婚也许会更加难;而婚姻本身,也从来就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