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剧变》将个人危机与国家危机相类比,这样的论断能否成立,依然存在争议。
作者 | 李明远
编辑 |韩方航
《枪炮、病菌与钢铁》作者贾雷德·戴蒙德的新书火了。这本名为《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的书,尝试解答危机应对这一关乎人类未来的重要命题。在今年4月出版后,因为恰逢全球疫情加速蔓延,而引发了更多关注。
无论是获得普利策奖的《枪炮、病菌与钢铁》,还是2005年出版的《崩溃:社会如何选择生存兴亡》,戴蒙德在自己的著作中都运用了科学加历史的跨界写作方式。《剧变》又把历史书写与心理学相结合。戴蒙德将心理咨询师掌握的12个影响个人成功应对危机的因素,引入了对7个国家危机的分析框架中,认为类比个人危机应对,可以帮助人们找到化解国家危机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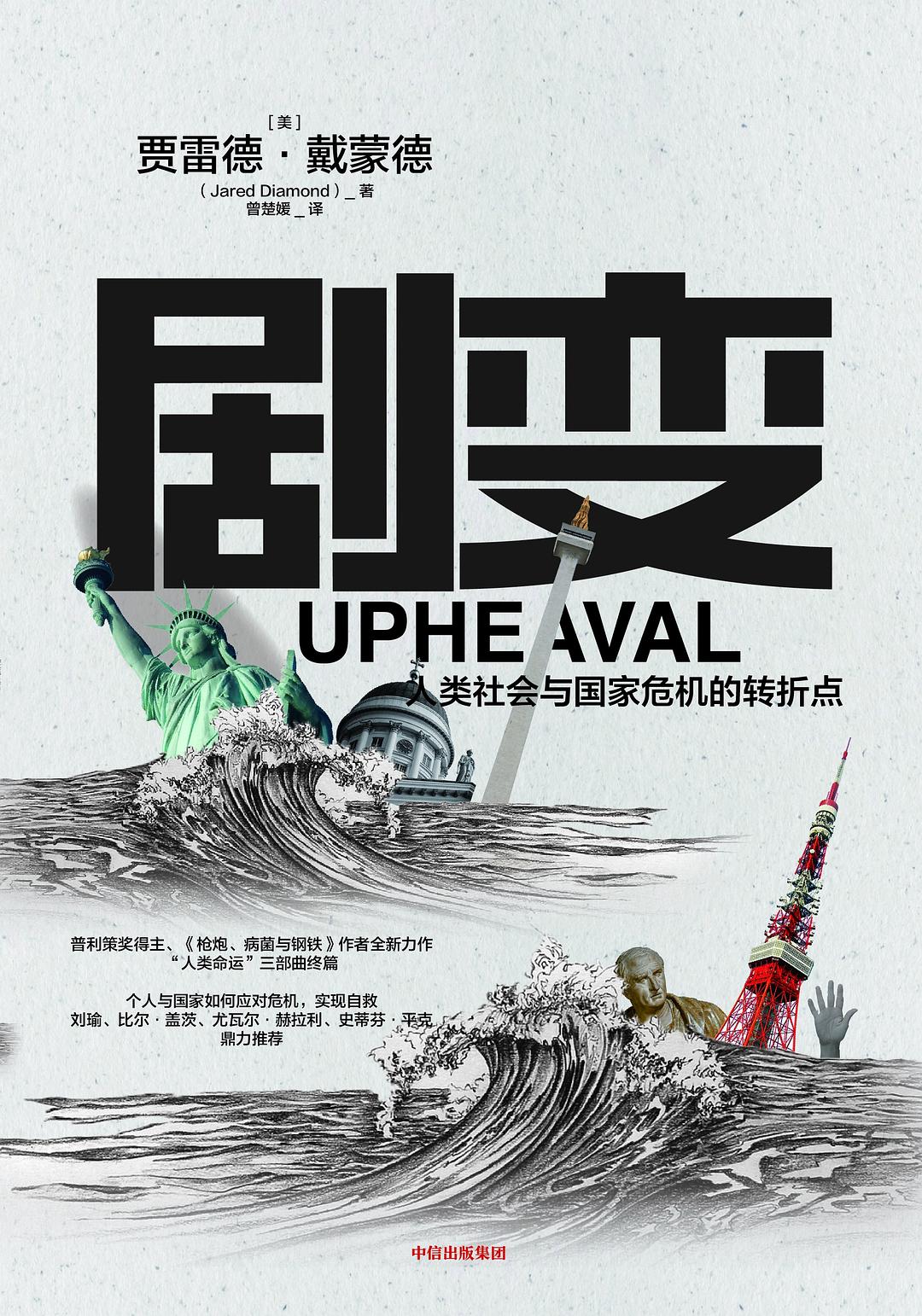
《剧变》中译本
今年83岁的戴蒙德长于大历史书写,作品重在考察文明兴衰,从长远的社会、经济结构观察历史脉动,知识维度跨越了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等多个学科。这是近年来非常流行的大历史写法,尤瓦尔·赫拉利的畅销书《人类简史》也属于这一范畴。
但是大历史的写作方法并非没有争议,学术界对于《人类简史》就有一些批评。《枪炮、病菌与钢铁》《崩溃》则可以被概括为复兴了地理决定论与环境决定论,这招致了学者诟病,指责戴蒙德忽略人类历史的复杂性。
这一次,《剧变》出版也难以避免争议。一些历史学家指出书中存在史实错误,削弱了这本书的可信度。更为重要的是,《剧变》将个人危机与国家危机相类比,这样的论断能否成立,依然存在争议。
大历史书写引入心理学视角
《剧变》作为戴蒙德“人类命运”三部曲终篇,延续了《枪炮、病菌与钢铁》《崩溃》两部前作的大历史书写风格。关于戴蒙德跳脱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壁垒的写作方式,有一句形象评价:“我怀疑贾雷德·戴蒙德实际上是一群各行各业的专家共用的笔名。”
戴蒙德不是典型的历史学家。他先是在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后来又在剑桥大学拿到了生理学博士学位,回到美国后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谋得教职。他兴趣广泛,工作后还发展了第二职业——鸟类学研究。50岁后,他又转向童年时的爱好,开始书写历史与地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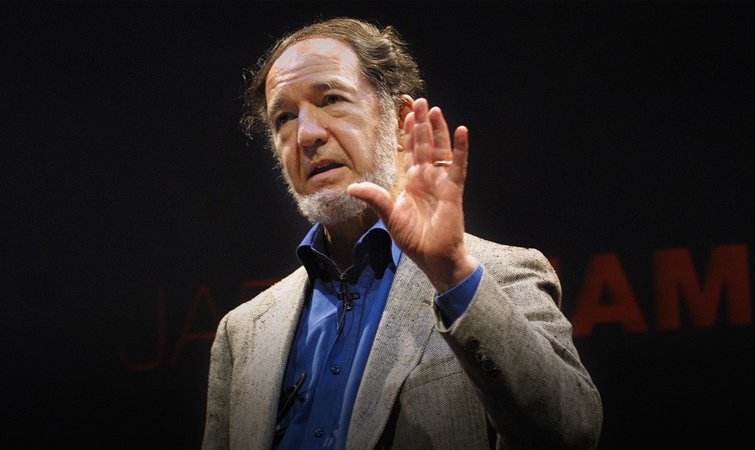
贾雷德·戴蒙德
1997年出版的《枪炮、病菌与钢铁》,解释了世界各国发展不均衡的原因。戴蒙德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民族环境的差异。书中,他运用了演化生物学和地质学等科学方法解读自己的观点。
《剧变》和两部前作一样,都采用了比较研究法,却改变了两部前作环境史的写作思路,抛开了前作运用纯熟的环境地理等分析变量,选择了心理学角度切入主题。
全书第一部分,戴蒙德借鉴心理学中个人化解危机的逻辑框架,提炼出影响个人与国家危机处理的12个因素。
1. 直面危机
2. 愿意承担责任
3. 明确问题的边界
4. 寻求帮助
5. 借鉴榜样
6. 自我力量/国家认同
7. 诚实自我评估
8. 应对危机的过往经验
9. 耐心
10. 自身灵活性
11. 核心价值观
12. 个人约束条件/国家地缘约束
《剧变》的创新之处在于提出了这样一种新的分析框架。但国家不是个人的放大化,二者明显在许多层面上各有特点。戴蒙德在《剧变》序言和第一章中,解释了通过个人危机视角去观察国家危机为什么有意义,这种方法有怎样的优点。
戴蒙德认为,对非历史学家来说,个人危机更贴近我们的生活,更容易被理解。从个人危机视角出发可使普通受众更容易联想到国家危机,从而弄清楚其中的复杂性。
在戴蒙德看来,这种类比的第二个优点在于,在个人危机的研究方面,人们已经取得不少成果,得出了个人危机的不同影响因素的发展路径,从而可以帮助人们理解个人危机的不同结果。这些因素提供了一个有利起点,使研究者可以着手描绘国家危机不同影响因素的发展路径,从而更好地理解国家危机的不同结果。
正是因为个人危机与国家危机之间存在这些明显的相似性、隐含的相近性和不同之处,戴蒙德认为将两者进行对比能够帮助人们理解国家危机。
缺乏统一的理论构建
“从个人危机的视角出发,可使普通受众更容易联想到国家危机。”戴蒙德运用心理学范式解析国家危机,对于大众的吸引力,被《剧变》出版后的市场反馈所印证。结合疫情危机阅读《剧变》的读者众多,让《剧变》在出版1个月内印刷了4次。
不过,《剧变》能否帮助读者弄清楚国家危机的复杂性,则要打上一个问号。人们结合疫情读《剧变》,似乎只是通过阅读,印证了自己已知的观念。比如危机应对12个因素中,“直面危机”“愿意承担责任”“诚实自我评估”等被一些国家忽略,导致了部分国家和地区疫情一度失控。
当戴蒙德尝试引入一种科学分析工具时,读者看到了涵盖心理学的12个因素。12个因素对于分析国家危机来说,这么多变量不是一个小数字。而且12个要素在具体国家危机案例分析中,又表现出没有高低之分的状态。这就让历史学家质疑引入心理学科学方法的意义。

2019年5月,比尔·盖茨与戴蒙德就《剧变》英文版展开对谈。
戴蒙德原计划在书中更为严谨的现代定量研究方法。但在花了几个月心思后,却发现这个任务只能留到以后的项目中去完成。一方面,他的样本只有寥寥7个国家,不足以得出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结论;另一方面,他曾尝试以数据资源为基础,来为部分变量建立可操作性指标,但后来他不得不放弃,因为那是一个巨大工程。
放弃了定量分析方法后,戴蒙德为《剧变》选择了历史学家传统的写作方式——叙述性写作风格。全书论证过程以散文式推理的方式来推进。《剧变》由此就失去了统一的理论构建,它读起来更像是案例分析集。
在《剧变》主体部分,戴蒙德用心理学家提出的12个因素作为框架,把芬兰、日本、智利、印度尼西亚等7个国家所面临的危机,以及各自的解决方式逐一分析,希望读者看出国家行为和个人行为之间的联系。
“我意识到一个痛苦的现实:因为这本书要讲7个国家,所以我对每个国家的描述都必须化繁为简。当我坐在书桌旁转过头去看时,发现身后的地板上堆着一摞摞书籍和文献,每一摞都有5英尺高,它们分别是每一章的阅读材料。”正如戴蒙德在序言中所坦承的,浓缩叙述历史的过程着实不易。
这样的历史叙述部分占据全书一半多篇幅,读者在其中往往看不到未被使用或未被充分使用的崭新历史档案资料。对于读者来说,这让《剧变》呈现出许多历史作品的特点,更聚焦于叙述,较少给出因果解析。《剧变》的价值落在了戴蒙德的占全书篇幅不多的历史解析,以及他穿插其中讲述的自己在7个国家的人生经历,对于后人有一定参考意义。
全球性危机难以找到解决方案
“新冠肺炎流行是一场悲剧,也是一次让世界变得更好的机会。”7月2日晚,一场主题为“全球疫情和危机管理”的对话活动在线上举行,贾雷德·戴蒙德向中国读者分享了对于疫情影响的看法,许多观点依然来自于他的《剧变》。
虽然普通读者乐于将《剧变》与疫情形势结合阅读,但《剧变》实际上更以单个国家危机问题为叙述对象。而每个国家与个人都要面对的这场疫情危机,实质上是个全球化问题。

面对疫情这场全球化危机,《剧变》的论述只点到为止。
《剧变》12章内容中,仅有第十一章《世界将去往何处》探讨了全球文明存续遭遇的威胁。这一部分曾点出,随着世界各地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紧密,新型疾病的传播成为全球化进程带来的一个意外后果。戴蒙德并没有在书中展开讨论传染性疾病。他只是表达了对于全球化的中性态度:全球化既给人类带来了问题,又提供了解决问题的路径。
现实中,戴蒙德由此出发的疫情分析,也不能提出明确的解决方案。在7月2日晚的对话活动中,戴蒙德对于新冠疫情带来的危机呈现出谨慎乐观的态度。由解决疫情开始,各国共同寻求危机解决方案,希望能成为今后所有国家和地区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模型。
此前,戴蒙德在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提出,疫情需要一个世界性的解决方案的表达。但是,无论是欧盟等政治一体化尝试的失败,还是疫情发生后各国出于本国利益需求采取的宽松不同防控政策,都说明了世界性解决方案这样表达的苍白性。
从这个意义上看,在因为疫情引发更多关注的《剧变》中,戴蒙德并未真正向世界提出更多新的洞见。如果读者对《剧变》探讨解决全球性危机问题抱有过高阅读期待,难免会感到失望。
如今,新冠疫情爆发,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为国家危机应对问题研究提供了充足的样本。未来如果有研究者能把《剧变》中的叙述性、口头性和定性分析,延伸为更严谨的量化分析,或许能够进一步让心理学范式展现出更高的价值。
从历史著作角度看,《剧变》或许只是售卖给普通读者的快餐知识书,而并不适合真正对历史抱有严肃学术追求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