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些关于秩序的不公和法律的无能,以及“世有良心者”无尽的批评疾呼,都已被雨果之笔永久地记录在案,不容抹去。
《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这部由维克多·雨果于 1862 年所发表的长篇小说,有另一个鲜为人知的名字:《法律的命运》。小说涵盖了拿破仑战争和之后的十几年的时间。故事主线围绕主人公罪犯冉阿让试图赎罪的历程,融进了法国的历史、建筑、政治、道德哲学、法律、正义和宗教信仰,堪称一部时代巨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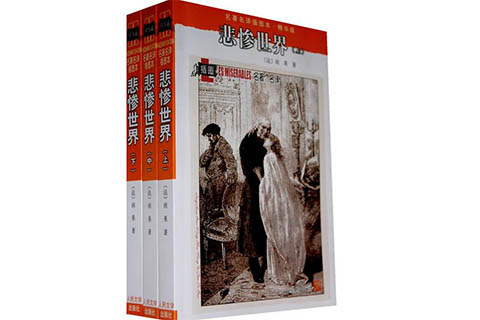
主人公冉阿让是个穷人,因为偷一条面包救济7个外甥,而被判五年徒刑。由于他不信服不公的法律,加上倔强不惧强权的个性,使他因屡屡越狱而致罪刑加重。身陷牢狱与手铐脚镣相伴十九年之后,他终于获得一纸假释令——然而这张黄色的自由状纸,并未让他在社会上取自由,反而处处引来歧视,使他流浪街头。
笛涅的主教米里哀好心收留了他。夜半时分,多年来穷困的习惯让冉阿让故态复萌,偷走了主教家的银烛台。不料半途被捕,警察将他送往主教家中对质,主教却没有揭发,反倒为他撒谎,说银烛台是赠送给冉阿让的礼物。警察悻悻然走后,冉阿让跪求原谅,撕碎假释信,发誓重新做人。
八年过去,冉阿让的确履行了当年的誓言。他易名为马德兰,成为了蒙特里市受人爱戴的市长兼工厂厂长,以慈善闻名。这时,工厂女工芳汀正遭受着凄惨的际遇。她年轻时遇人不淑,生下女儿珂赛特后只能独力抚养。重病临死前,她将珂赛特托付给得知真相后的冉阿让照顾。

故事中的正义代表是刑警沙威。他坚信法律的正确无误,也相信公正必须以铁血捍卫,而慈悲宽恕只会滋生更多的犯罪。对于“逃犯”和屡次越狱的冉阿让,他无法原谅、深记在心,誓将其抓回牢狱。事有凑巧,当他在蒙特里市怀疑冉阿让就是他追查的逃犯时,昏庸低效的刑警们却抓到了长相相似的流浪汉商马第——他受诬偷苹果而被捕——警察、法官和证人竟然一致认定,他就是那个逃脱的苦役犯冉阿让。
冉阿让得知此事后,不愿让商马第替自己受牢狱之苦,毅然来到法庭,承认自己就是冉阿让。此时的沙威,已多次目睹冉阿让高尚的人格,最终决定放他生路。然而身上所压的司法与正义枷锁,使沙威内心备受煎熬,投河自尽。
雨果是浪漫主义文学代表之一。浪漫主义得以产生的前提,在于它和启蒙思想联系在一起,是文学民主化的表现之一;但另一方面,浪漫主义恰恰将重点放在了个体与整个世俗化社会的抗争上——这是浪漫主义一个非常有趣的表现:呈现这个社会,是为了更好地与之抗争。

早在1840年,当雨果拟定《悲惨世界》的框架时,他将小说划分为“一个圣人的故事”、“一个男人的故事”、“一个孩子的故事”和“一个女人的故事”等四个部分。这四个故事构成了小说的主体内容。与这四个故事相似的众生相,则构成了那个时代法国的真实原貌。与《巴黎圣母院》将叙事时间定格在十五世纪路易十一治下不同,《悲惨世界》的叙事时间是雨果真正的“当下”,他从一八一五年写起,主要的叙事时间延伸至一八三二年巴黎起义。
1862年1月1日,《悲惨世界》在被他称为“奥特维尔别馆”的住所问世。彼时,雨果正身处流亡之中。为了保障家人返回巴黎后的生活,他需要为这部新著卖个好价钱。此时,有个叫拉克卢瓦的比利时出版商,主动找上门来,打算以30万法郎(约折合现在600多万欧元)购下此书12年的版权。然而他读完书稿后,感觉处处是沉重,景景是悲凉。特别是雨果在书中以写政论般的激情,大段大段地抨击时弊,解构人性,批评法律。于是他建议雨果对这些段落进行删节。雨果坚决拒绝,“轻快而肤浅的喜剧只能获十二个月的好评,而深刻的戏剧则会获十二年的成功。”
最终,拉克卢瓦同意一字不改地出版此书。果然,《悲惨世界》一问世即大获成功。六年之内他不但收回所有投入,还净赚51万7千法郎(约折合现在1000多万欧元)。而《悲惨世界》显然不是仅像雨果所说的,获得“十二年的成功”——它被多次改编为电影或戏剧。至于今天的法国,尽管已经沉重或轻巧地翻过了这一页,但那些关于秩序的不公和法律的无能,以及“世有良心者”无尽的批评疾呼,对穷人命运的同情,都已被雨果之笔永久地记录在案,不容抹去。
或许正如他在《悲惨世界》序言中所言:“只要因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的意义来说,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