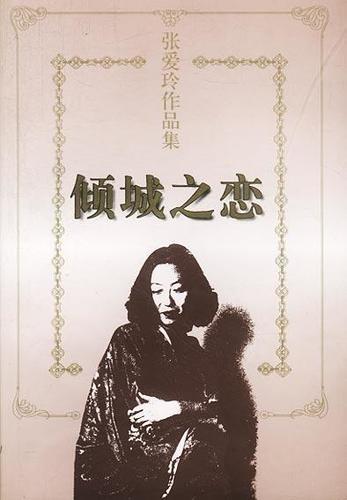
浮华背后的苍凉爱情。
《倾城之恋》被视作张爱玲短篇小说中最脍炙人口的一篇,发表于1943年,属于汪精卫时期的上海文坛,同时也是张爱玲开始在文学刊物上发表成熟中文的创作的第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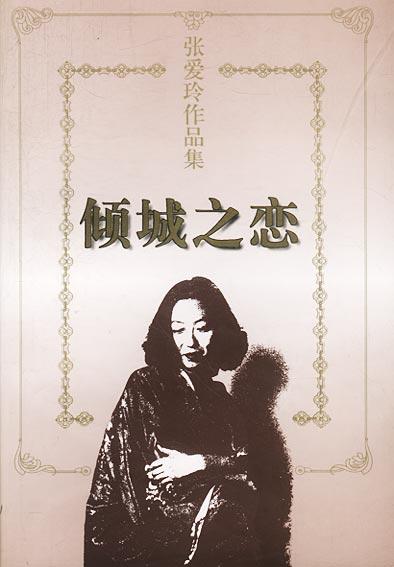
作者:张爱玲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出版年:1997-3-1
故事发生在香港,上海来的白家小姐白流苏,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身无分文,在亲戚间备受冷嘲热讽,看尽世态炎凉。偶然认识了多金潇洒的单身汉范柳原,便拿自己当做赌注,远赴香江,博取范柳原的爱情,要争取一个合法的婚姻地位。两个情场高手斗法的场地在浅水湾饭店,原本白流苏似是博输了,但在范柳原即将离开香港时,日军开始轰炸浅水湾,范柳原折回保护白流苏,在生死交关时,两人才得以真心相见,许下天长地久的诺言。
死局终于下成了和棋。
乍一看是个挺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在“浪漫”的外壳下,张爱玲完全颠覆了才子佳人的传统,浪漫的爱情、为爱牺牲一切的勇气在这里不复存在。“倾城”是倾一座城(香港沦陷),成全一双人,而不是歌颂至高无上的爱情。
这恐怕是张爱玲一直擅长的——在文中写尽一切关系:男女,女人,父母子女,主仆……无不彻骨清醒而到残酷的地步。在《写〈倾城之恋〉的老实话》一文中,张爱玲说:“写《倾城之恋》,当时的心理我还记得很清楚。除了我所要表现的苍凉的人生的情义……”。由此可以看出,她并不是想创作出一个英雄美人或才子佳人的故事,而是要表现出“苍凉的人生的情义”。在描写范白的感情时,也不是浪漫的男欢女爱,而是一 场又一场你来我往的算计。
在《自己的文章》中,她再次提到《倾城之恋》:“从腐旧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将她感化成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 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也只能如此。”
身前身后,张爱玲于中国现代文学都可以说是没有同类的“异形”。她是谜。是符号,永久横亘在争论两端。几乎没有一个作家——无论男女——像张爱玲这样被一些人书写成文学神话,甚而有如遗迹挖掘一般的“张爱玲学”,同时又被另一些人批评为怨妇写作误上神坛。在不同的时代,她的作品连着她的人生都在被不断复写、补白和重构,满足着不同人的不同偏见。
“张迷”对她的出身十分熟悉: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祖母李菊藕则是李鸿章长女。母亲黄素琼的家族也不普通——张爱玲的曾外祖父黄翼升祖籍长沙,跟随曾国藩湘军征战太平军,最后官至长江水师提督。张爱玲自小到大都在写她的高门巨宅。6岁写了第一个故事,情节是年轻女子趁她哥哥不在家,设计了一个曲折阴谋来对付她的嫂子;7岁写了一部家庭悲剧小说。
18岁那年,她被父亲毒打禁闭,逃到母亲和姑姑处生活,却发现母亲因她的累赘而脾气变坏。她不怕写出后来母女之间那种互憎和绝望:“越是痛苦,越是可耻。我们是在互相毁灭,从前我们不是这样的。”
上世纪40年代早期,张爱玲不过20多岁,即以小说集《传奇》和散文集《流言》“成名要趁早”地横空出世于上海沦陷时期文坛。1943年,张爱玲交给《紫罗兰》月刊主编周瘦鹃两部中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一个星期后,周瘦鹃告诉读后感:觉得它的风格很像英国名作家毛姆的作品,而又受了一些《红楼梦》的影响,“不管别人读了如何,而我是‘深喜之’了”。在1944年《倾城之恋》和《金锁记》发表后,她天才的名气已经令上海滩惊艳。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夏志清在1961年发表英文著作《中国现代文学史》,里面给了张爱玲42页篇幅,并将她排到鲁迅之前,甚至称她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华语文坛一时耸动。
“张爱玲热”一直持续到当代。宋淇之子宋以朗在其父母去世后成为张爱玲新的文学遗产执行人,陆续授权出版了她生前未曾发表的遗稿。据宋以朗2010年述:“随着《重访边城》、《小团圆》、《异乡记》、《张爱玲私语录》、《雷峰塔》和《易经》的问世,张爱玲再一次成为大众焦点,其人气之盛甚至比她生前有过之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