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创团队面对的挑战是,把握原著用自由写压迫的基调、用彩色描绘灰暗的意味,对乌托邦世界加以批判,但挑战失败了。
数字图书馆古登堡计划最近发布了一组平面广告,用涂黑书页上文字的方式,向观众展现,改编自名著的电影删去了多少重要情节。被涂黑书页的《野性的呼唤》《爱丽丝梦游仙境》《圣诞颂歌》,影视化后原文损失比例分别为:75%、71%、51%。
按这种方式计算,最近上线流媒体平台Peacock播出的美剧《美丽新世界》,原文损失比例至少85%。最为遗憾的是,当经典被一顿“魔改”之后,不但没有迈向另一座高峰,而且沦为大杂烩。在这部剧中,你看得到原著大框架,也看得到《饥饿游戏》《西部世界》的影子,故事主线则失控沦为一个三角恋故事。
《美丽新世界》最终被拍成赫胥黎在书中写到的“感官电影”——剧情简单,充斥情欲和暴力。原著中的反乌托邦主题,在剧集中体现得不鲜明。原著党不买账,阅片量大的美剧迷也嫌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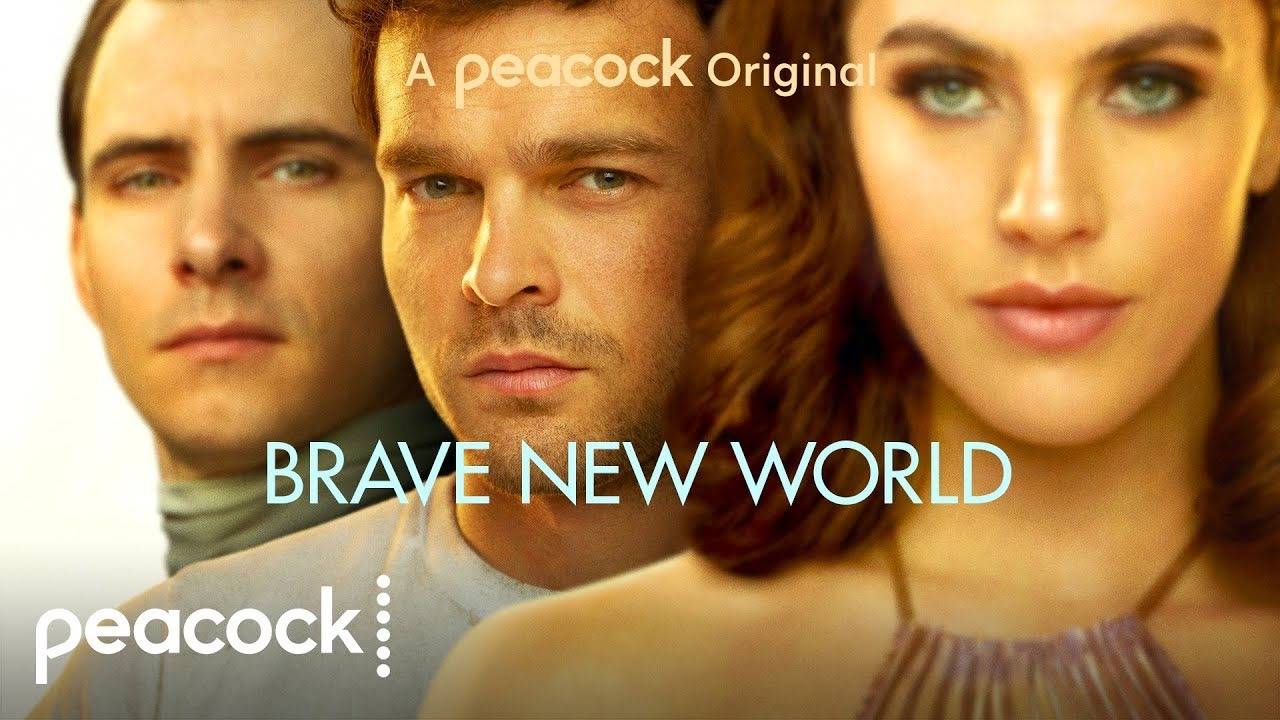
《美丽新世界》预告海报,故事主线变成一段三角恋。
视觉奇观只够撑两集
在小说《美丽新世界》中,英国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畅想了一个表面幸福、稳定的乌托邦。在未来世界,伦敦人被按照阿尔法、贝塔、伽玛、德尔塔和埃普斯隆不同等级进行标准化培育,人们不再遵循一夫一妻制,吃一克有麻醉作用的苏摩药片就能产生幸福感。故事主线则讲述了从野蛮世界来到伦敦的“野人”约翰,陷入原始社会与乌托邦的两难境地,最终走向自戕的悲剧结局。
作为一部寓言小说,《美丽新世界》并不以故事情节与角色取胜,而是以世界观见长。它的人物角色并非魅力十足,剧情也并不引人入胜,却靠着赫胥黎构建的乌托邦世界奇幻氛围,让读者欲罢不能。《美丽新世界》文本上的特点,令它成为一部难以进行影视化改编的经典小说。
而原著伟大之处,在于赫胥黎1931年的写作,用缜密思辨预见了科技进步对于人类个体的影响。其中许多设定与判断,在当下看来依然具有批判意义。剧集《美丽新世界》保留了原著大框架,就拥有了一个成熟的未来世界内核,起点较高。
剧集将含蓄的文字呈现得更为直观:未来都市新伦敦生活流光溢彩,人们夜夜笙歌,沉迷于性事与服用苏摩药片。人们物质生活富足,没有一夫一妻,个人长期独处不被鼓励,忠诚于一位伴侣的倾向也会被监察与矫正,年轻男女最好频繁更换伴侣。人们有明确等级,但不同等级的人接受自己的身份设定,彼此相安无事。

内置眼球的镜片,能帮助新伦敦市民实时在线联系。
《美丽新世界》出版近90年后,电话、电视、电影等都不再是新鲜技术。剧集用视觉特效包装出新伦敦,在改编时升级了角色的科技装备。人们为眼球戴上一个镜片,就能实现全息投影般的视频通话,也能瞬间识别每个人分属的不同等级。这些关于未来都市的设定,都让观众在最初追剧时,有一种新鲜感与趣味性。

每个人的等级差别,能通过内置眼球的镜片直接看出。
然而,当观众逐渐接受了未来都市的设定,新伦敦所呈现的视觉奇观,就无法再作为吸引观众的元素。从某个角度来看,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由娱乐主导的世界,万物互联下人们获得虚拟的快乐,隐私的匮乏、人们对于欲望的放纵等时代特征,都在无限逼近剧中的乌托邦世界。剧中视觉奇观下,本质上反映了我们当今的生活日常,习惯了便无甚新鲜感。
主创团队面对的挑战是,把握原著用自由写压迫的基调、用彩色描绘灰暗的意味,对乌托邦世界加以批判,但挑战失败了。
剧集线索混乱反倒凸显原著经典之处
小说改编为影视作品,并不需要完全照搬原著,但对于经典名著来说,忠实原著改编的好处是降低烂尾危险性。《美丽新世界》原著结局,对乌托邦提出反抗与质疑的“野人”约翰因为“众人皆醉我独醒”,最终走向自杀。如果剧集忠实原著改编,这部剧将呈现大时代倾轧下的小人物悲剧。
然而,《美丽新世界》的改编没有遵循这条干净利落的主线。编剧显然更有野心,希望架构起鸿篇巨制,为这部剧未来的续订铺路。在剧集中,有三股不同的力量反抗乌托邦。但三条线互相干扰,让剧集高开低走。
第一条线,是《饥饿游戏》式的。在新伦敦之外,剧中存在的另一个世界——荒蛮之地冒险乐园,保留着一夫一妻、胎生等生活方式,被新伦敦人作为参观落后生活方式的旅游地点。新伦敦人到冒险乐园参观,把那里生活的人们称作“野人”。新伦敦市民伯纳德·马克思和女友列宁娜·克朗,到蛮荒之地度假,却偶然卷入野人发起的叛乱。在血腥屠杀中,两人被野人约翰救了出来,他们一起逃回了新伦敦。

荒蛮之地是剧中新伦敦之外另一个的平行世界。
“文明”与“原始”两个世界正面冲撞,给观众带来的爽感陡增,让人以为一场《饥饿游戏》式的反抗压迫革命即将打响。但从第三集开始,故事舞台移回了新伦敦。野人叛乱的线索自此断掉,直到最后一集尾声才再出现。
接下来,全剧篇幅最多的第二条线——一场三角恋故事开启了。这条线本意是展现个体对于新伦敦世界观的困惑与不满。但编剧选择了用感情线,营造约翰身上的摇摆感。抽掉剧集中的科幻外壳,这场绵延数集的三角恋,与最俗套的偶像剧并无区别。
剧中的第三条线,是约翰在摇摆之中触发的新伦敦最底层人群的觉醒。埃普斯隆群体因为身份最低微,从来都是干着最累的活。到全剧尾声,他们从蒙昧中觉醒,要摆脱阿尔法、贝塔等上层人群的控制,开启自我生活。这条故事线与《西部世界》非常相近。
不过,编剧设计的这三条线,都有共同的缺陷:少见深入的批判。这令全剧到处都是断掉的线索。剧集不但毁掉了原著面貌,也没能创造出一套逻辑自洽的世界观,徒留了一场场给观众带来感官刺激的滥交场面。美国《娱乐周刊》评论文章的标题是:《美丽新世界》充斥药品、性爱和摇滚乐,但没有灵魂。
相较于美剧,赫胥黎在文字上的批判走得更深。《美丽新世界》出版27年后,他在1958年又出版论著《重返美丽新世界》,运用丰富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知识,比较了现代社会与他在《美丽新世界》中所构想的寓言图景。他提出,《美丽新世界》写到的过度组织化、独裁体制下的政治宣传、洗脑教育、化学劝诱等,都在从预言变为现实。重温论著,人们对赫胥黎的洞见更能感同身受。
时隔近90年改编《美丽新世界》,如果剧集能集中发力,深入剖析阶层固化、娱乐至死等某个现实问题,或许我们才能看到更有力度的作品。如果说美剧《美丽新世界》真有什么价值,那就是它能更吸引一部分观众去阅读原著,进而体会原著的经典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