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雪山崩塌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因为雪花犯下的是“平庸之恶”。
文/全历史 蓑笠寒江雪
1906年10月14日,美籍德国犹太思想家、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出生。
她是大哲学家海德格尔(此处可a至1976年5月26日的弗莱堡)的弟子,也是“轴心时代”的提出者雅斯贝尔斯亲自指导的哲学博士。她是20世纪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和政治理论家之一,她对纳粹主义的深刻反思,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如今她的思想也成了学者们研究的热门。
那么,她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首先,她是一个敢爱敢恨,拿得起放得下的独立女性。
阿伦特18岁上大学,情窦初开,很快就与一个青年教师发生了恋情。这个老师比她大17岁,已婚,而且有孩子,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这是她第一次遇到火热的爱情,所以特别投入。但没过多久她就意识到这个感情不会有结果,因为海德格尔不会为她抛妻弃子,他正在为评职称而专心写作,所以故意冷落阿伦特。

阿伦特很坚强,以冷静的态度和行动来摆脱感情的困境,既然拿得起,也要放得下。她选择走出这段感情的阴影,转学到另一所大学,从此很少和海德格尔见面。后来海德格尔投靠纳粹,两人才彻底决裂。但十几年过去后,两人再次面,阿伦特一笑泯恩仇,和海德格尔恢复了朋友关系,还为他在纳粹统治期间犯下的错误而辩护。
阿伦特一辈子结过两次婚。她的第一任丈夫之所以和她离婚,据说是因为受不了她像男人一样抽雪茄。不过她最终还是找到了对的人,就是她的第二任丈夫布吕赫,两人白头偕老,生活幸福。

其次,她是受纳粹迫害的犹太难民。
阿伦特出生在德国中产阶级犹太家庭,原本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是纳粹的崛起破坏了这种美好。上小学时阿伦特就能感受到身边人异样的眼光,但她并没把这太当回事。直到博士毕业,她才真正感受到纳粹主义的可怕。因为是犹太人,所以她被取消了学术研究的资格。
希特勒上台后,迫害犹太人的行动更加激烈,阿伦特走出书斋参与到犹太组织中,帮犹太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移民,结果被盖世太保抓进了监狱。好在抓她的人不是特别坏,关了8天之后就把她给放了,这才躲过一劫。
为避免再次受到纳粹的迫害,阿伦特流亡到了法国巴黎。在法国谋生,阿伦特吃了不少苦。她做两份帮助犹太人移民的工作,生活暂时得到了保障。在巴黎的这段时间,她认识了许多富有同情心的法国作家,如加缪(此处可a至1960年1月4日的维勒布勒万)、萨特(此处可a至1905年6月21日的巴黎),还有同为流亡者的犹太知识分子本雅明。他们经常在咖啡馆中相聚,正是在这个团体中,阿伦特找到了归宿,并且与本雅明建立起友谊。后来法国沦陷,为躲避迫害,阿伦特又移民美国。当时本雅明将包括《历史哲学论纲》在内的所有手稿交付阿伦特。阿伦特托人出版了本雅明的《历史哲学论纲》,而本雅明则因为过境失败而服毒自尽。
最后,她是反抗“平庸之恶”的天才女思想家。
阿伦特十三四岁就开始阅读康德(此处可a至1804年2月12日的柯尼斯堡)、克尔凯郭尔的哲学著作,18岁时考入马堡大学哲学系,成为了海德格尔的学生。后来还听过现象学之父胡塞尔(此处可a至1859年4月8日的普罗斯尼兹)的课,最后跟随雅斯贝尔斯学习,22岁就获得了博士学位。有三位大师做自己的老师,想不成思想家都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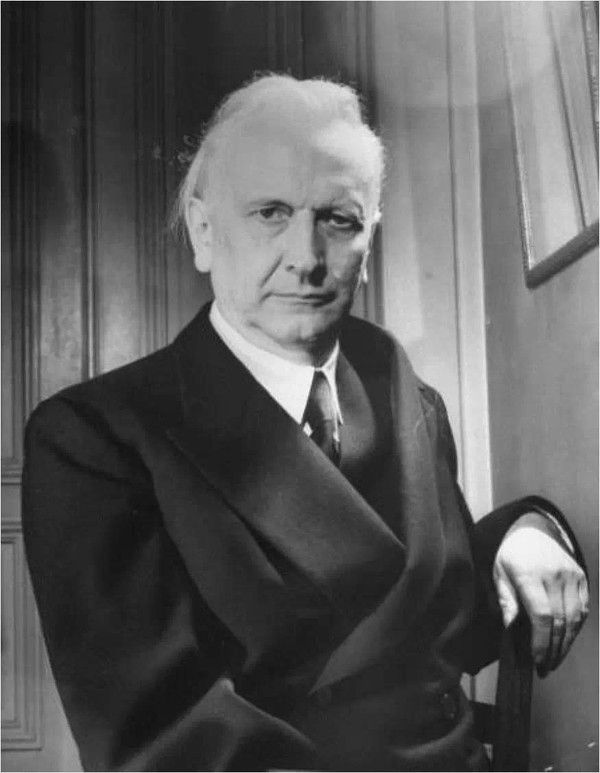
但是阿伦特的巨大影响不是在严格的哲学领域,而是集中在对纳粹罪行的反思上,因为她本身就是一个受害者,后来她知道纳粹在集中营干的事更加罪恶滔天,她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于是开始系统研究纳粹主义。
阿伦特认为,纳粹主义的罪恶有两种,一种是极权主义统治者本身的“极端之恶”,代表人物是希特勒;另一种是被统治者或参与者的“平庸之恶”,代表人物是艾希曼。希特勒大家都熟悉,艾希曼是谁呢?他是一个曾负责运输和屠杀犹太人的德国军官,被捕后受审,阿伦特亲往现场,发现艾希曼只是一个性格温和的普通人,看起来并不像一个心理变态的杀人狂,阿伦特把艾希曼这类人的恶归纳为“平庸之恶”(也译为“恶之平庸”)。

阿伦特认为平庸之恶比极端之恶更为可怕,因为它就潜在于普罗大众之中,一个热爱家庭、热爱工作的人也可能盲从于极权主义统治者,变成一个执行命令的刽子手,艾希曼就是这样的人。(详见规律31 - 群体敢作恶:好人为什么会变坏?)
那么如何反抗“平庸之恶”呢?
阿伦特提出的办法就是思考和行动,她认为艾希曼就是缺少思考的典型。她说的思考是一种开放性的思考,要与他人对话,自己也要反思,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苏格拉底的“助产术”,在与别人辩论的过程中吸纳不同意见,最后达成共识,此时内心是和谐统一的。而它的反面是不对别人的观点提出异议,这样人的内心是没有反思的,实际上也不会和谐统一。她说的行动也包含在这个过程中了,就是在公共舞台上敢于发言、挑战和接招,彰显做人的尊严。
她不仅这么说,也是这样做的,她经常参加聚会,参与社会活动,表达自己的观点。
历代评价
1、阿伦特生存的基石就是一种对真实的执着,她是作为本来意义上的人而存在的。
——雅斯贝尔斯
2、她固然不是那类埋首于专业的麻木的学者,但也不是那类与时俱进的聪明的学者,而是逆流而上的反抗的学者。她反潮流,反抗她的时代,因为她确信,她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极端的时代,黑暗的时代。
——林贤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