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与古代政统
黄帝因身具众多功德,很早即被祭祀,如至少列于包括五帝三王在内的春秋祀典之中。当时制定祀典的原则是:“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扞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即必具德业功烈之人方可入祀典。黄帝作为此祀典第一人而被祭,乃因“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
《国语·鲁语上》,即黄帝为万民作器物及财殖生计的开发供给做出贡献。后来有“黄帝三年”传说,孔子解释说:“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
《大戴礼记·五帝德》,是可见黄帝功德惠利影响之久远,其为世人祭祀纪念是必然的。《史记·封禅书》:“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按此乃秦汉所祀五色五方帝,与《月》五帝相关,乃上帝,与春秋时祀典之人文英雄黄帝有异。
黄帝被推上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的崇高地位,主要是司马迁的功劳;司马迁这样做,是受孔子儒家多方影响启发的结果。即经孔子、司马迁二人前后的努力使黄帝最终定位于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的位置上。秦汉王朝的建立,使大一统规模空前扩大,汉武帝时儒家《公羊传》大一统之义,尤其受到弘扬推重,受此启发,司马迁决意撰《史记》,为黄帝迄刘汉的大一统局面提供史学论证,即建立一部以帝王政统为代表的王朝更替信史,使历史与现实之间互为阐发参证。为此他首先撰成《五帝本纪》,置于《史记》之首,《五帝本纪》内突出对黄帝的塑造,把他叙述成首位大一统格局开创者的帝王政统角色代表。《五帝本纪》宣扬五帝同祖论,把黄帝塑造成中华民族始初的人文共祖。
《五帝本纪》的撰成,尤其是黄帝作为帝王政统开创者的角色,使汉武帝时代代表的汉王朝大一统局面,得到了史学文化上的反映释读,这其中司马迁较多受孔子儒家的影响启发。
关于《五帝本纪》的撰写,他在其结尾赞语中写道:“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
司马迁作《史记》从资料乃至观念上多受孔子儒家的启发影响,意在作一部大一统背景下帝王政统更迭的王朝信史,为此,他在黄帝身上寄寓颇多。经过他修史过程中的多重努力,钩稽考索,访察实证,对历史传说中的黄帝深致改造重塑功夫,使之成为一个颇具历史地位和历史影响的历史人物。最主要的,是他借五帝同祖论把黄帝推上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的象征地位,黄帝因此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象征性开端。
黄帝与古代历法及音乐
古代记载黄帝使其臣下制历法。
《世本·作》“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桡作甲子,隶首作算术,容成综此六术,著调历”(雷学淇校辑本)。(按《吕氏春秋·勿躬》:“大桡作甲子,黔如作虏首,容成作历,羲和作占日,常仪作占月,后益作占岁”,并不言此诸人为何世,此则一并言为黄帝之臣,殆与黄帝制历说之影响有关。)
上举制历诸臣之外,尚有风后于制历关系密切。《后汉书·张衡传》:“元初基,灵轨未纪,吉凶纷错,人用朣朦。黄帝为斯深惨。有风后者,是焉亮之,察三辰于上,跡祸福乎下,经纬历数,然后天步有常,则风后之为也。”李注:“《史记》曰:‘黄帝迎日推策,举风后,力牧以理人,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又曰:‘旁罗日月星辰’。《春秋内事》曰:‘黄帝师于风后,风后善于伏羲氏之道,故推演阴阳之事。’《艺文志》阴阳流有《风后》十三篇也。”此言黄帝制历,风后乃其制历重要助手之一,(《淮南子·览冥》:“昔者黄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辅之,以治日月之行律,治阴阳之气,节四时之度,正律历之数。”
黄帝制历,风后之外,又包括力牧,太山稽,合上《世本》之言,则黄帝之臣几全部参加,可见黄帝制历乃一大事。马王堆帛书《十大经·立命》:“数日,历月,计岁,以当日月之行。”乃谓黄帝制历之事,且所制为阴阳合历。)且指明其天文星占的性质,所言很重要,深合古代历法的性质。
察《史记·历书》及《天官书》,天文历法被用于禨祥星占的性质,极为清楚。考黄帝所制似为五行历法。《史记·五帝本纪》记黄帝“治五气,艺五种”,即黄帝与五行相关。《五帝本纪》又谓黄帝“有土德之瑞”;黄本为“中”之色,故《月令》黄帝为中央之帝,皆可证黄帝与五行之关系。《史记·历书》又谓“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是黄帝又与五行历法之制定相关,此见于《管子》。其《五行》曰:“昔黄帝以其缓急作五声,以政五钟。令其五钟,一曰青钟大音,二曰赤钟重心,三曰黄钟洒光,四曰景钟昧其明,五曰黑钟隐其常。五声既调,然后作立五行以正天时,五官以正人位。”此五钟、五声、五官皆五行观念,其中重要者乃“作立五行以正天时”,以下所述五行历法即是。其五行历之代表时日为“甲子木行御”“丙子火行御”“戊子土行御”“庚子金行御”“壬子土行御”。此五行历分为五季,各 72 日,各有当季应行之时令,性质与《礼记·月令》相似,只不过其五行五季与《月令》四时十二月形式上不同。
《淮南子·天文》亦记有五行每行各主 72 日之时令制,与《五行》相类,应同为黄帝所“作立五行以正天时”之历制,亦可与上引《历书》“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相证。《历书》此言又可与其所引汉武帝太初改历诏书所言相证,其诏曰:“盖闻昔者黄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验,定清浊,起五部,建气物分数,然盖尚矣。”其中多难解之历法术语,综据《集解》《索隐》,所言乃黄帝制历之事,亦应为五行历法。
《封禅书》亦见黄帝制历之传闻,其曰:“齐人公孙卿曰:‘今年得宝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与黄帝时等。’卿有札书曰:‘黄帝得宝鼎宛朐,问于鬼臾区,鬼臾区对曰:黄帝得宝鼎神策,是岁已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纪,终而复始,于是黄帝迎日推策,后率二十岁复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黄帝仙登于天。’”详鬼臾区所言,多历法专门术语,大要乃言黄帝制历事,但却由此引出“黄帝仙登于天”的结果。
《封禅书》所言多鬼神封禅事,亦多杂黄帝神仙事。其可注意者乃将封禅、制历与黄帝神仙事相混杂,是乃方士窃儒生受命、改历、封禅之说而不通,又欲迎合秦皇、汉武求神仙之旨,阿谀苟合,误衍讹传所致。但可借之考见黄帝制历的传闻。又《封禅书》所言,可与《五帝本纪》谓黄帝“获宝鼎,迎日推策”相比证,综据其《索隐》、《正义》所言,即黄帝制历之事。故黄帝制历之事,《五帝本纪》与《封禅书》所言前后互见相证。
在有关东汉天文律历的记载中,亦涉及张寿王所治黄帝历相关情况。东汉灵帝熹平四年朝廷议历,五官郎中冯光、沛相上计掾陈晃主甲寅元,蔡邕以为:“今光、晃各以庚申为非,甲寅为是。案历法,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凡六家,各自有元。光、晃所据,则股历也。他元虽不明于 图谶,各[自一]家[之]术, 皆当有效于当时。[武]帝始用太初丁丑之元,六家纷错,争讼是非。太史令张寿王挟甲寅元以非汉历,杂候清台,课在下第,卒以疏阔,连见劾奏,太初效验,无所漏失。是则虽非图谶之元,而有效于前者也。”(范晔《后汉书》引司马彪《续汉书·律历志中》)按甲寅元见于图谶《考灵曙》《命历序》,东汉崇尚谶讳,故议者认为当用甲寅元,反对章帝以来的庚申元,是以蔡邕有此议。
《汉书·律历志上》载张寿王治黄帝《调历》,此谓“张寿王挟甲寅元以非汉历”,则黄帝《调历》应与甲寅元有相合者。按四分历经章帝元和、和帝永元时始定,《考灵曜》《命历序》甲寅元“所起在四分庚申元后百十四岁”(范晔《后汉书》引司马彪《续汉书·律历志中》),所以“张寿王挟甲寅元以非汉历”,应为东汉人据图谶追述前事。考黄帝等六.历中之股历用甲寅元,“黄帝造历,元起辛卯”(范晔《后汉书》引司马彪《续汉书·律历志中》),故张寿王所治亦非纯粹的黄帝《调历》,所以《汉书·律历志上》又谓“寿王历乃太史官股历也”。又因冯光、陈晃以股历甲寅元非难章帝以来四分庚申元,是以蔡邕此处重提“太史令张寿王挟甲寅元以非汉历”的旧事。
但据《汉书·律历志上》张寿王不但非议太初历,又“寿王猥日安得五家历”,应即寿王坚持六历中的黄帝历而非议其他五家。那么,张寿王所治《调历》亦非纯粹黄帝历,或杂有股历内容,但对此他自己并不十分清楚,是以非议包括殷历在内的其他五家历。《汉书·律历志上》又谓张寿王言“传黄帝《调律历》,汉元年以来用之”,乃误说。因为汉初承秦乃用颛頊历,故当时史官已驳正,即《律历志上》谓“案汉元年不用黄帝《调历》”,那么,张寿王历学知识亦多杂驳者。似此皆已无从详考。但从汉代的历议之争,可见黄帝历在当时是颇有影响的历法之一。
黄帝与阴阳五行思想之合流
《管子·五行》记黄帝得蚩尤明天道,得太常察地利,得奢龙辩东方,得祝融辩南方,得大封辩西方,得后土辩北方。是为黄帝得六相。六相各有知识专长,于是据此各使任职,即蚩尤明天道使为当时,太常察地利使为廪者,奢龙解东方使为工师,祝融辩南方使为司徒,大封辩西方使为司马,后土辩北方使为李。若使四方之职与四时相配,则春者工师,夏者司徒,秋者司马,冬者李。此以天地与四方组配,由于四方又可与四时转换,故天地亦可与四时相组配。在古代四方、八方与四时、八节(即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相对应,由于时间、空间有对应的转换关系,故四时与四方及八节与八方间可相互转换,于是天地四方与天地四时概念相当,亦皆为典型的阴阳家概念体系。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提到阴阳家时,指出其以“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为教令大纲,其中更以天地阴阳四时最为根本。(见泷川资言等《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此教令大纲各项,均与天时节候相关,是阴阳家思想特征的反映。
在《周官》中见到的是天地春夏秋冬六官体制,此六官体制明显具有阴阳家色彩。《周官》中所见宇宙世界框架乃天地四方六面立方体,反映出天地四时与天地四方的对应关系。如《周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封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相应如《春官·龟人》亦以天地四方名六龟之属。
天地四方是与阴阳家相关的较早概念,在《尚书》中又见上下四方。如《吕刑》:“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洛诰》:“惟公明德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又《仪礼·觐礼》:“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设六色,东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黄。设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东方圭。”是此上下四方即天地四方。又《荀子·儒效》:“至高谓之天,至下谓之地,宇中六指谓之极。”杨注:“六指,上下四方也。”上下四方即天地四方,若以四方配四时,又可谓之天地四时,此天地四方或天地四时乃阴阳家的宇宙世界 框架。《管子·四时》日:“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是阴阳即天地,四时即阴阳,天地、阴阳、四时乃阴阳家思想纲纪。《淮南子·时则》:“制度阴阳,大制有六度:天为绳,地为准,春为规,夏为衡,秋为矩,冬为明堂之制,静而法准,动而法绳,春治以规,秋治以矩,冬治以权,夏治以衡。是故燥湿寒暑以节至,甘雨膏露以时降。”按六度即天地四时,明堂乃典型阴阳家政救圣堂,天地四时乃阴阳家纲纪大法,此大法明则四时寒暑和美,雨露膏泽顺降。所谓六度,说明阴阳家的宇宙世界框架乃天地四方,其呈现六面立方体之状;阴阳则乃此世界万有运行法则的变化调节内在动因。
天地四方相当于一个六面立方体,乃是从观念上对宇宙世界自然空间的三维立体模仿,具有自然哲学的思维特点。与五行相当的五方乃中央对四方的二维平面图,它相当于天地四方六面体中的天地维合并为一点后所形成,具有社会人事设计层面的意义。由天地四方三维立方体变为对五方二维平面图的设计崇尚,与人们的思维变化有关。即天地四方本是对兼容万有的宇宙世界自然容量框架的理解认同,随着居中而治的政治意识强化,于是中央统括四方的平面布局,成为与集权需要更相适应的观念形式。于是对五行方位的平面设计崇尚,取代六面三维立方的自然世界框架而得到突显。五行方位突出的是中央,四方降为对中央的附从地位,因而它更符合中央集权的政治崇尚。中央与四方的关系,具体到五行方位中,即以土居中, 木火金水分居东南西北四方。黄帝作立五行已见于前文所论黄帝五行历之内,此处拟专论五行方位以四方分属之势突显中央地位之尊。《管子·四时》日:“中央曰土,土德实辅四时入出……其德和平用均,中正无私,实辅四时……国家乃昌,四方乃服。”按“实辅四时”乃谓土居中,兼主四方。《汉书·律历志上》:“中央者,阴阳之内,四方之中,经纬通达,乃能端直,于时为四季。”此将中央对四方的地位优势讲得极明白,尤其“阴阳之内,四方之中”一句,将中央扼天下核心枢纽的冲要地位,讲得更明白。“四季”乃谓土主四时,使四时之末凑集于中央而附属之。《太玄·太玄数》:“五五为土,为中央,为四维。”郑万耕注:“四维,谓四季。维,指四角。木火金水配春夏秋冬,土无所配,又四时兼主,即寄于季春、季夏、季秋、季冬。”此亦为土居中,兼主四时四方;所谓“四季”乃土兼主四时四方之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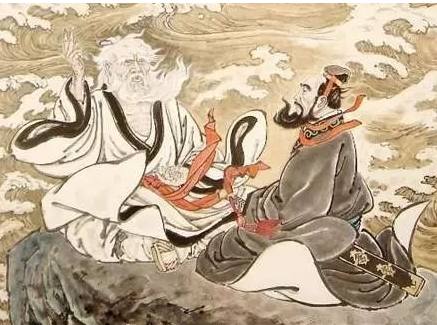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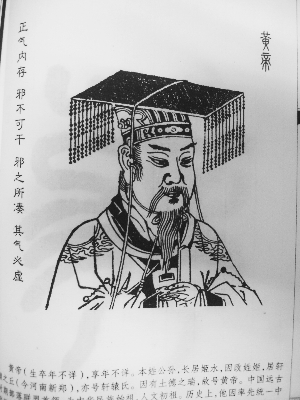
以上尝试对天地四时代表的阴阳思想与五方五行思想,各从义理层面加以诠释,并企望对两种思想图式的先后兴替关系作出解释说明。由于二者在《管子·五行》中还是以各自独立的形态被叙述,即黄帝得六相与黄帝作立五行二者分述,那么,这里所表现的仍是二者密切融为一体化之前的阴阳五行思想,阴阳与五行仍未达到深度的一体化形态,二者间仍有某种隔阂在。但二者既同在黄帝的名义下被述及,那么,黄帝在阴阳五行思想形成发展中的地位,亦因此可明。《汉书.艺文志》中以黄帝命名的阴阳家著作唯《黄帝泰素》二十篇,班固自注说为“六国时韩诸公子所作”,师古注引刘向《别录》:“或言韩诸公孙之所作也。言阴阳五行,以为黄帝之道也,故日《泰素》。”尽管《黄帝泰素》二十篇可能为依托,但若结合《管子·五行》所述,刘向所谓“言阴阳五行,以为黄帝之道”的意义,颇值得深思。此外,在《艺文志·数术略》五行类亦著录《黄帝阴阳》二十五卷,《黄帝诸子论阴阳》二十五卷。按《诸子略》阴阳家同《数术略》五行类固不可在学术上相提并论,但说明传黄帝技艺诸术中亦包括数术五行。(数术五行中除上言《黄帝阴阳》等两种外,尚有《诸子论阴阳》二十五卷,《太元阴阳》二十六卷,《三典阴阳谈论》二十七卷,《阴阳五行时令》十九卷。即数术五行中亦融入五行阴阳,是乃数术略中的五行阴阳,与诸子思想中的五行阴阳是不同的,二者之别是“学”与“术”的差异。如果说《诸子略》是“学”的话,《数术略》只能是“术”,由此决定二者间的基本区别)总之可以认为,黄帝同阴阳五行思想的关系是多方面的,黄帝学派在阴阳五行 思想深度体融合的过程中,亦应起到过他们所能起到的推动作用。(《汉书·艺文志》著录之书以黄帝命名者颇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