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之际,若论厉害角色,你会想到谁?项羽、刘邦?那是当然。张良、韩信、萧何?建国三杰,名垂万世,这也毋庸置疑。陈平?嗯,既聪明,又有趣。范增?好个老头儿,可惜,遇人不淑。除这几位外,再来,你还会想到谁?
我想说曹参。
曹参?除了成语“萧规曹随”之外,许多人提起曹参,恐怕,就是一片模糊吧!这样的模糊,其实一点儿没错,甚至,也可以说是对的。因为,曹参的厉害,正在于他的无所作为。曹参的了不起,也恰好就因他无可称述、难以形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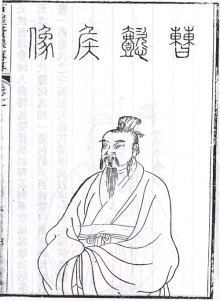
但是,曹参在历史舞台的上半场,却大有作为、颇可一述。他先是岀将,而后入相;将军曹参,征战沙场,“凡下二国,县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将军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马、侯、御史各一人”,战功彪炳呀!同时,曹参在厮杀冲突之间、出生入死之际,也“身被七十创”。因此,汉初封侯,论及位次,立下汗马功劳的大臣纷纷力主曹参应位先萧何,名列前茅;理由是:曹参披坚执锐,攻城略地,“身被七十创”,萧何呢?如此战绩,当然了不起。但这功勋,虽说烜赫一时,然若置于历史的长河中,却影响有限。恐怕只需七八十年,至多一两百年后,大概就鲜少有人在意这样的角色了。毕竟,真论决定性战功,异姓为王如韩信、彭越等人,肯定都远比曹参重要。但扣除最关键的韩信之外,即使彭越,在后人看来,不过也就是个次要角色,何况曹参?
换言之,这么显赫的战功,毕竟只是一时之事;就长远来说,将军曹参,其实并没那么重要。但是,后半场的相国曹参,尽管无可称述、难以形容,却在历史的长河中有着“光而不耀”的特殊分量。这分量在于:从相国曹参身上,我们总算可以具体地明白:什么叫作“无为而治”。
曹参为相,凡一十二年。相齐之初,厚聘胶西盖公为师。礼敬之隆,甚至将堂堂相府正堂,都改成了供养盖公的住宿处所;如此优礼,显然是当初一见,盖公三言两语,便打到曹参要害,将他最关切之处都清楚点了出来。盖公不仅提示曹参如何在齐地“安集百姓”,更指点曹参在汉初形势下如何进退用藏。于是,盖公为言黄老之道,既说人道,亦言天道;既言臣道,亦谈君道。从此,曹参“如齐故俗”,一切因之循之,以清静为本;他如江如海,也藏污,也纳垢,即使奸邪之人,亦容之蓄之,不惊不扰。九年之后,“齐国安集,大称贤相”。同时,他虽位列开国功臣,却以无名为令名;安稳沉静,不落机巧。日后,刘邦对功臣多有猜忌,即使忠勤如萧何,也一度受拘被执。可偏偏曹参从不受疑,亦不遭忌;他吉祥止止,连个事儿也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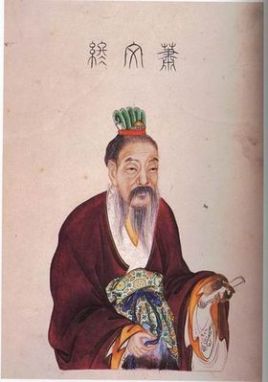
刘邦死后,又两年,曹参继萧何为相,“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既无变更,自然不兴不革,根本就无所事事。于是,属下与群僚见曹参这般“日夜饮醇酒”,毫不作为,大都深感不妥、亟思劝谏。结果,一见曹参,才欲开口,曹参便招呼饮酒。喝一段落,想开口再言,曹参又频频劝饮。一饮再饮,最后酒醉而去,终究不得而言。曹参相汉,如此三年。后来,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评曹参,“不变不革,黎庶攸宁”。曹参死后,百姓则歌曰,“萧何为法,耩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
这样的“不变不革”与“守而勿失”,乍看之下,颇是容易;似乎只需竟日醇酒,沉湎其中,然后一切不管即可。但若细细想来,却又实实地不然。试想:任何人高居相位,总揽天下之际,可能会毫无兴革吗?毕竟,人多有私心,当官的更有权力欲望;位高权大如相国,随便起个心念,天下都要为之震动;有兴有革,一来可证明自身能力,二来不也彰显了自己的分量?再者,人总有一己想法,也总有爱憎好恶,一步步走到相国高位,更免不了会有满肚子的理想与抱负;新相上任,基于使命感,即使不觉得百废待举,至少也颇感处处有待改进。于是,在准备一展抱负之时,必然有改革,也必然有更张,又怎么可能彻底依循、毫无改变呢?
因此,曹参的“不变不革”,看似愚钝,实则有莫大之智慧;他的竟日醇酒,貌似滑稽不经,但骨子里,却有一番深谋与远虑。曹参之所以无所事事、毫不作为,固然有鉴于秦法过严过密,“民苦秦苛法久矣”;也固然是因萧何规模已定,“法令既明”;但是,关键仍在于曹参既明人道,亦明天道。他明乎天人,故不以一己私意扭曲天道。时势若该休养生息,便绝不妄加兴革,也不随意滋事。换言之,曹参面对天道时,可以将私心与权力欲望节制到近乎“无我”,也可以把爱憎好恶与理想抱负化除到近乎“无执”。就一般人而言,真要节制私心与权力欲,其实不太容易;若要去除理想与抱负的执着,更属难得。但也唯有真做到如此,“不变不革”,才庶几可能。

于是,曹参清静无为,一切沿用旧章,紧接着,他只找“对”的人来做事。曹参从郡国之中,挑选官吏,只要是“木诎(同木讷)于文辞,重厚长者”,一旦发现,便马上起用,“即召除为丞相史”:相反的,若是“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则一概摒弃,“辄斥去之”。
从此,曹参的政府里,尽是一群不惊不扰、不务声名的厚重长者。他们既不严苛,也不以法逼人(不死守法律,更不把“依法行政”挂在嘴边)。他们不求表现,也不贪图绩效(曹参不可能弄评鉴、搞评比)。他们默默做事,老老实实;外表是个官员,性格则近于老农。这一群厚重长者,一个个光而不耀;他们是,暧暧内含光。
这样的暧暧内含光,一时间,遂成了这新朝的气象。虽然曹参只任汉相三年,但典范一立,不仅养成汉朝的宽厚之风,更养足了两汉气脉。于是,我们今天看到汉陶与汉砖,也读到汉简与汉碑,那里头,都有种曹参无为而治遗留下来的“无用之大用”,名曰,质朴与大气。于是,有汉一代,前后绵延四百年;即使后来被篡,直至西晋末年,匈奴人刘渊称帝,仍因人心思汉,依然要建国号为“汉”。又于是,我们今天自称汉族,相较于全世界骤然而兴又骤然而衰的诸多民族,汉民族不仅几遭颠踬旋即又勃然而兴,汉文明更是气息深长、绵亘久远。而今,在百年倾颓之后,汉文明又要初初重建;这时,回头再看看曹参,除了“萧规曹随”一词之外,我们还能读出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