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晋楚城濮之战被誉为影响中国古代史上的“决定性会战”,春秋时期强盛的楚国迅速向中原地区扩张,直接威胁到了包括周王室在内的中原诸侯国的安全,并且与日益勃兴的晋国形成战略对峙,面对楚强晋弱的形势,晋国决策层上下一心,精诚团结,充分利用“软实力”,运筹帷幄,逐步建立起有理有利有节的战略优势,于公元前632年借助“退避三舍”的计策,诱敌深入,在城濮大败楚军,阻止了楚国势力的北扩,最终奠定了晋文公春秋霸主的地位。
“在本质上,中华先秦时代的国际关系与近现代的国际关系是相同的。”作为运用“软实力”推动国家崛起的经典案例,研究城濮之战的历史教训,有利于我们从历史经验中正确看待当下国际竞争特别是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软实力”的问题。笔者拟从春秋时期的国家关系、城濮之战的历史教训以及对“和平崛起”的启示三方面,管中窥豹,予以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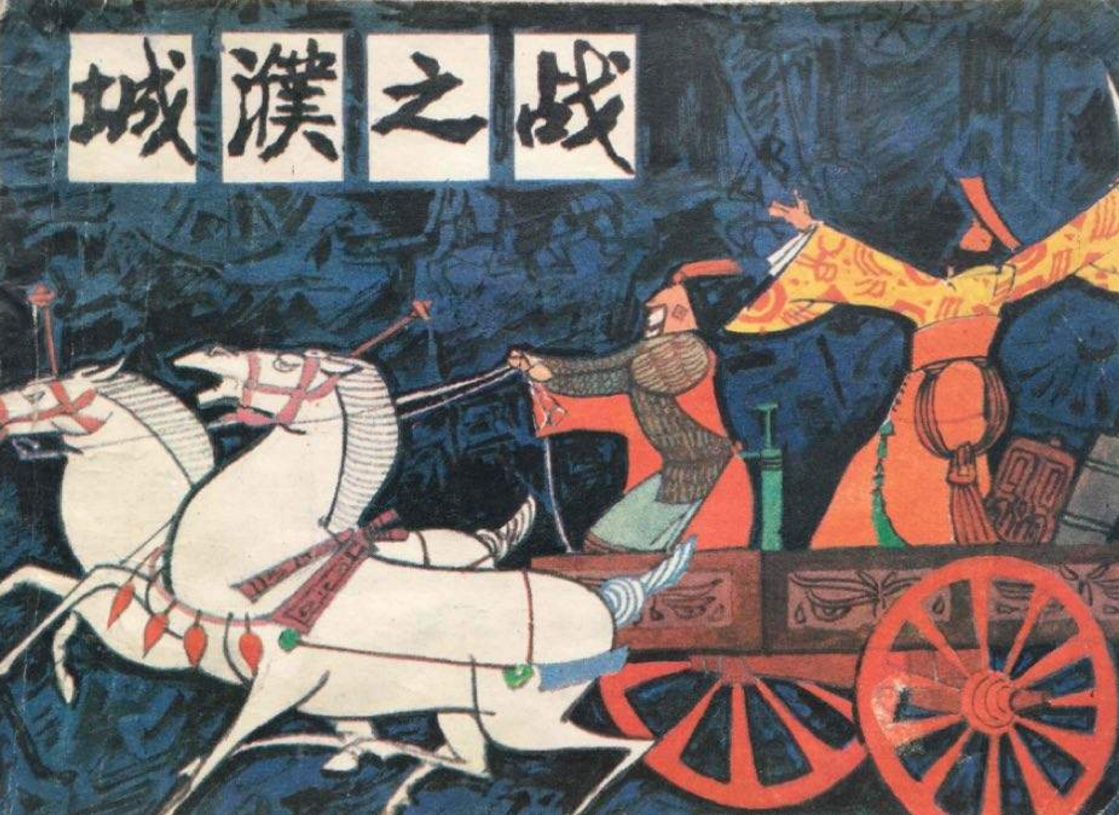
一、2500年前的“联合国体系”——“先秦国际关系史”
“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诗经·小雅·十月之交》的这句话,早就被用来形容春秋时期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就记载:春秋时期“弑君三十六,灭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如此纷乱的社会中,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成为历史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关节点。周王室与诸侯的关系、诸侯之间的关系变得尤为紧张复杂,从而缔造了具有特色的“先秦国际关系史”。
春秋列国争霸“从本质上讲,是诸侯争当周王室的代替者,争当中心或者中央。在这一时期,列国争霸的霸主制度为中国维持了相当程度的秩序,避免了无中心 (中央) 后的大混乱”。参照今天的国际形势,春秋时期列国之间纷繁复杂的关系产生了丰富程度不亚于当代的形形色色的对外政策和战略,“在某种意义上,春秋时期形成的华夏体系有点像今天的联合国体系”。具体表现为:
(一) 东迁后的周王室“相当于一个联合国的旗号,所有国家都是联合国里的一个成员国,在这个体系里面,有一些基本的国际法准则,首要的维护周王室的存在”。对比今天联合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不难看出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晋国大夫赵衰言:“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周晋同姓,晋不先入王,后秦入之,毋以令于天下。方今尊王,晋之资也。” 表明当时要成为大国,必须要尊重周王室,主动承担相应义务,才能赢得“称霸”的政治声望;这与今天日本谋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从而实现其政治大国理想的做法是相通的。
(二) 整个春秋时期,大国为争夺霸权征战不休。但是列国中的大国在整体上是势均力敌的,彼此间保持着战略力量平衡。当时的任何一个大国都没有强大到可以不考虑其他大国反应而单独行动的程度。城濮之战前晋国极力争取齐秦两国支持就是明证。春秋时复杂多变的大国关系让我们看到了今天“一超多强”大格局下的多极化国际社会的影子。
(三) 齐桓公有“葵丘之会”,晋文公有“践土之盟”。“如果体系内成员碰到外部敌人的入侵,就是所谓的周边野蛮民族的入侵,那么这个联合国的成员有义务互相帮助。”这些盟会体现了在春秋时期的诸侯霸主寻求在自己的领导下建立一致对外的“集体安全模式”的尝试。而春秋中后期晋楚之间召开的两次“弭兵之会”,也表现了当时斗争尖锐的大国之间已经具备通过建立“战略对话机制”来“增信释疑”,寻求双赢局面的先见之明。
正如有学者所言:“中华先秦的国际关系与近现代西式的国际关系没有根本的不同,核心都是战争与和平,都是围绕战争的原因及和平的条件展开的。”正是春秋时期国家关系与近现代西式国际关系在本质上的某种相通性,决定了对于春秋时期列国争霸历史的深入研究,有利于从中借鉴历史经验的精髓,从而更好地认识把握当前多变的国际形势。而晋楚城濮之战作为春秋时期最大规模的一场战争,开创了晋楚争霸中原的历史格局。研究城濮之战对于学习认识“先秦国际关系史”,无疑具备总揽全局,提纲挈领的重要意义。

二、城濮之战双方对于“软实力”运用的历史教训
“软实力” (soft power) 是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约瑟夫·奈在15年前首次提出的概念,约瑟夫·奈在《注定领导:美国力量变化了的特性》一书中是这样界定“软实力”的: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通过吸引而非强制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的能力,即“罗致行为能力”。一般来讲,软实力发挥作用依靠的是说服别人跟进、效仿或者使其同意遵守由拥有巨大的软力量的国家主导下的国际规则、国际制度和国际体系。具体来说,“软实力”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二是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三是外交政策的道义和正当性;四是处理国家间关系时的亲和力;五是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的吸引力;六是对国际规范、国际标准和国际机制的导向、制定和控制能力;七是国际舆论对一国国际形象的赞赏和认可程度。
可见,“软实力”是现代国际关系格局下的产物,那么2500年前的中国春秋时期,是否存在“软实力”呢?答案是肯定的。前面已经讲到,中国先秦时期包括春秋时期在内已经具备了和近现代西方国际关系格局类似的国际政治体系。在《左传》中有关城濮之战的内容中,共出现“德”6次、“礼”9次、“信”3次,这些文字的背后反映的就是城濮之战中双方在“软实力”上的较量。
(一) 时代背景:楚国的扩张与晋国的勃兴——楚蛮与周礼的“文明冲突”
《史记·楚世家》中记载:楚国的始祖鬻熊是芈姓季连部落酋长,参加了灭商的斗争,受到周王室的重视,故给予“子”的封号,臣属于周。但是“周之宗盟,异姓为后” (《左传·隐公十一年》) ,楚是周王朝的异姓封国,受封的爵位也低,一开始就受到周天子的歧视。楚人自然对此仍耿耿于怀。起初王室强盛,尚可震慑,可到了西周昭王时,双方实力已此消彼涨,结果昭王征楚“南巡不返”。从此周王朝由盛而衰,楚国则日益强大,逐步走上与周王室分庭抗礼的道路。到春秋时,楚国继续做大,熊通“王不加位,我自尊耳”自立为楚武王;后楚国尽吞“汉阳诸姬”;成王时泓之战又大败宋国,到城濮之战前,“上无明天子,下无贤方伯,强楚主会”。楚国北进一时无任何阻力,对中原诸夏构成严重威胁。
晋国是西周初年分封的姬姓古国,其始祖叔虞为周成王幼弟。西周末年,晋文侯拥戴平王东迁洛邑,为东周的缔造立下大功,受到平王奖赏。春秋初期,晋国内部出现公室与贵族争夺君位的长期斗争。经过六七十年,才以旁枝取代大宗,重新建国。新建的晋国充满活力,晋武公之子晋献公大力扩张,后因争夺君位,导致晋国15年的内乱,晋献公之子重耳在外流亡19年之久才最终由秦穆公派兵护送回国接管政权,即晋文公。仅仅四年时间,继位时就已62岁的晋文公就领导晋国快速崛起,对内对外都取得了巨大成就。此时中原诸国群龙无首,唯有晋国有实力与楚国逐鹿中原。
城濮之战前晋楚两国的对峙,实质上是两种不同文化扩张摩擦融合的必然产物。
尽管东迁后周王室的实力一落千丈,但是它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首先,它是华夏国家联合的政治符号,在对付诸蛮狄夷戎部族的入侵和进攻时,周王室是一面旗帜,表明华夏诸国与非华夏部族的区别;而且它是春秋时期的文化中心,是各诸侯国的共同的意识形态,是春秋时期以周朝典章制度为中心的华夏文化的主要传播者和制造者。”
周王室的独特地位和影响力让争霸的大国必须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晋文公继位次年,晋出兵平定周王室内乱,护送周襄王回到都城。晋文公的“尊王”之举包括城濮之战后献楚俘于周王的行为表明:在城濮之战中,晋国是以周王室乃至整个中原诸侯代表的身份来进行战争的。晋文公本身又是姬姓宗族,是周襄王的“叔伯”,而且他继位前19年的流亡生涯中,在各国都留下极佳声誉,这都极大提高了“国际舆论”对晋国“国际形象的赞赏和认可程度”。这点连楚成王都用“有德不可敌”加以肯定。晋文公城濮之战可谓“师出有名”。
反观楚国,如前辈史家张荫麟先生的形容:“楚人的生活充满了优游闲适的空气,和北人的严肃紧张的态度成为对照。”楚人拥有独特的文化体系,在扩张过程中又总以周王室的对立面出现。因此当楚向中原文化的腹地扩张时,必然会遭到中原地区主流文化的强烈反弹,可见楚国当时不具备“文化价值上的感召力”。而且“昭王南征不复”的史实也对楚国的“国际形象”有极大损害。城濮之战的导火线——宋叛楚通晋,宋成公这样做除了现实的利益考虑,很大程度上跟宋晋在文化上“同根同源”有关,这正是“软实力”的体现。
(二) 城濮之战:“刚而无礼”同“能以德攻”的较量
《左传》对于城濮之战有完整记述,但对具体战况的记述仅123字,可谓简略。大部分笔墨都用在描绘战前双方的运筹帷幄上。诚如古今东西方战略家所达成的共识:战争的准备往往比战争本身更加重要,而在战争准备时,精神又似胜于物质。分析双方战争准备过程,晋国在政治体制、外交、宣传各个方面都占据优势。《孙子》云:“胜兵先胜而后求战。”晋军可谓胜兵,楚军可谓败兵。晋军的取胜理所应当。
(1) 政治体制:晋楚在体制上的差距首先体现在主帅的选用上:楚国统帅子玉“刚而无礼”,无视楚成王“无从晋师”的命令,对战争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晋方统帅先后是“说礼乐而敦诗书”的郃谷和“上德也”的先轸,从史书中的评语就能看出双方主帅在口碑上的差距。更重要的是:晋国在整个战争中君臣团结一心,政治体制相当民主,群臣敢于直言,君主更能察纳雅言。反观楚国,任用子玉时是“国老皆贺”,只有年轻的蒍贾言其必败,难道是国老们都老眼昏花集体失察?实际是碍于子玉是重臣子文所举荐,不敢明说罢了。楚国国老的趋炎附势与晋国大夫赵衰举荐不曾追随晋文公流亡的郃谷为主帅的大度形成鲜明对比。最致命的是,楚成王战略决策摇摆不定,却无人直言明示,最终造成子玉孤军深入。而晋国君臣对此战准备充分,志在必胜,晋文公每每犹豫摇摆之时,总有大臣敢于指点迷津。《国语》中记载:“是师也,唯子玉欲之,与王心违……楚师必败。”这番话恰恰出自城濮之战前投奔晋国的楚人王孙启之口。“楚材晋用”,正是晋国综合国力特别是“软实力”强大的表现。
(2) 外交策略:城濮之战前晋楚两国拉拢分化其他诸侯国的外交行动也是双方角力的焦点。起初,晋国在外交上处于“楚一言而定三国,我一言而亡之”的被动地位。但是晋国决策层在认识到这一点后很快就展开了一系列外交行动。晋国一方面将计就计,用“银弹攻势”离间了楚与齐秦两国的关系,杜绝了腹背受敌的可能。另外分化瓦解楚国战略联盟,曹卫两国先后“告绝于楚”,楚国的战略联盟被彻底拆散。从而根本上改变了“背惠食言,以亢其仇”的不利外交局面。《春秋》中记载:“晋侯、齐师、宋师、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除晋楚外,春秋五霸中其余三国都站到了晋的一边。外交战略如此成功,焉有不胜之礼?而楚国在外交上不懂得运用结盟,常贪图小利而失大势,最终落得孤立无援的结局。
(3) 舆论宣传:晋国在舆论宣传上最为成功的例子就是“退避三舍”。晋文公流亡楚时,曾受楚成王的厚待,如晋国大臣子犯言:“背惠食言,以亢其仇,我曲楚直。”晋文公庇护背叛恩人的叛徒,按道理说是“不仁不义”。但是晋军退避三舍。一方面是避敌锋芒;更重要的是,诱使急于求战的楚军主帅子玉做出“君退臣犯”的不义之举。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仍离不开“礼”的约束。而春秋时军队人数较少,通晓“礼”的贵族、平民又占相当大的一部分。违背战争中的“礼”,会造成军人的思想混乱,对战争是否符合“礼”产生怀疑,对军队的战斗力有直接的打击。所以到开战,“楚众欲止,子玉不可”。兵将已经不再一心。晋国的宣传战,营造了有利于晋国的良好舆论,更扰乱了楚军军心。可谓是一箭双雕。
战端未开,晋国就已经赢得先机。诚如《左传》所言“吾且柔之”,正是晋军的以柔克刚之策,“能以德攻”,奠定了城濮之战晋军胜利的基石。
(三) “践土之盟”——将军事胜利转化为政治胜利
城濮之战意义重大,城濮之败是楚国争霸道路上的严重挫折与损失。但是城濮之败,对楚的打击更多是心理上,对其国力之减弱亦属有限。因此晋文公借助城濮之战,“取威定霸”的关键在于其后的“践土之盟”,正是晋文公通过“践土之盟”的一系列行动,使自己的霸业达到顶峰,展示了其运用 “软实力”的高妙之处。
此次盟会,周襄王策命晋文公为“侯伯”,并给了晋文公“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王慝”的任务,晋拥有了代表周王室行使征伐大权的“尚方宝剑”。实际上晋文公把自己放在以“周礼”为代表的主流社会文化秩序守护者的地位。而将楚看作“主流社会文化秩序的破坏者”。春秋时期的国际关系上,一方面是激烈残酷的厮杀征战,另一方面则是竞争的上空飘扬着尊礼扶周的旗帜。春秋五霸相继而出,无不是打着“尊王攘夷”的牌子,挟天子而令诸侯的。不论是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还是晋文公“求诸侯莫如勤王”的策略,概莫如此。
晋文公正是利用周王室在“文化价值的感召力”,将军事胜利转化为政治胜利。从根本上奠定了日后晋国称霸中的政治资本。

三、城濮之战中 “软实力”的运用带来的现实启示
(一) 城濮之战中晋国的胜利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的胜利
晋国 “一战而霸”。其关键就是把重点放在了自身实力特别是“软实力”的发展上。晋文公继位后不仅重视经济、军事的发展,而且特别注重“文之教也”,教导人民知义、知信、知礼。在物质上、精神上、制度上都做好了称霸的准备。所以,正是晋文公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才奠定了“政平民阜”的称霸基础。
尽管当前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大有提高,但中国还将长期坚持邓小平同志制定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中国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必须首先做好自己的事情,而这个事情之中的重中之重。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当前不仅要继续稳步增加“硬实力”,“软实力”的建设也需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夯实“软实力”的基础,避免犯类似于前苏联的因为没有“软国力”的相辅相成,片面追求以GDP为中心的“硬国力”发展而造成被国际社会孤立的历史错误。
(二) 城濮之战中晋国的胜利是正确运用国际 “游戏规则”的胜利。
春秋时期,尽管诸侯大国屡抗王命,但是周天子名义上“共主”的地位还无人敢取代,周“礼”仍然是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遵守“礼”就是遵守国际规则,违反“礼”则可能引起重大国际纠纷,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整个城濮之战中,晋国始终能够巧妙运用遵守国际准则,赢得了“外交政策的道义和正当性”。提升了“处理国家间关系时的亲和力”,所以能够得到周王室和中原诸国的支持。
中国的“和平崛起”意味着中国不能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期待世界“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是需要保持长期稳定的和平国际环境和国际体系。这就要求中国应更加积极参与现有国际规则,融入现存国际体系。对于现有国际规则中不尽公平合理的部分,首先要参加进去,才能从内部加以改造,也就是说,中国要“学会作国际体系内合法的忠诚反对派”。历史教训告诉我们,21世纪中国要利用国际准则、规则和组织为自己创造有利条件,做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中流砥柱,而不是下一个国际秩序挑战者。这关系到21世纪中国发展的全局战略。
(三) 城濮之战中晋国的胜利再一次证明“软实力”的运用是以硬实力为基础的
古往今来,任何试图崛起的大国都必须经历血与火的洗礼,城濮之战中的晋国也是如此,战争是真刀真枪的较量,晋国的胜利,一方面得益于对“软实力”的成功运用,更离不开“硬实力”的巩固发展,正是晋国在晋文公领导下地飞速发展,才奠定了晋国在诸侯国间长袖善舞,纵横捭阖的基础。
纵观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的风雨历程,就更能深刻体会到“硬实力”和“软实力”间唇齿相依的关系,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经济水平明显落后于其它大国,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没有今天这样重要,这是为什么?关键是“硬实力”的缺失,正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当我们的“硬实力”足够强大之后,中华民族的“软实力”才有基础,才逐步在世界文化之林中愈发光彩夺目。中国要真正完成“和平崛起”,一方面要让“软实力”真正“软下去”,更要让我们的“硬实力”真正“硬起来”。
(四) 城濮之战中晋国的胜利本质上是文化的胜利
春秋时代大部分时间所谓霸权均赖晋国维持。梁惠王向孟子所云,“晋国天下莫强焉”,因为这一超级强国的存在,遂能北面阻止狄人南侵,南面阻止楚人北上,西面阻止秦人东进。随着当时中原华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融合,以地理位置、文化程度、血缘关系三要素为区分标准的“华夷观”逐渐被以文化为区分标准的“夷夏观”取代。每当强大诸侯崛起,他们都力求摆脱自己的夷狄身份获得诸夏认同 (如:秦楚吴越) 或者向夷狄开战以服人心 (如:齐晋) ,体现出当时的共同的“文化认同”。可见晋文公能赢得了周王室和其它中原诸国的支持,就是利用了文化的凝聚力、吸引力和感染力,晋国的胜利本质上是文化的胜利。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以其博大精深的文化深深地吸引着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并对这些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世界文化的繁荣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努力提升国家“软实力”,增强中华民族文化的吸引力,让世界了解中华文化,认同中华文化,这是构建良好国际环境,让中国“和平崛起”的需要。就像有学者描绘的那样:“几十万美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南非和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在中国的高等学府求学,世界顶尖学者竞相申请到北京、上海、香港、台北进行学术交流、开办讲座,各国政界、工商界领袖以获得中国大学授予的名誉学位为莫大荣幸,21世纪中国真正强盛的标志不是航空母舰在四大洋游弋,耀武扬威,而是孔子所说的‘近者说 (悦) ,远者来’。”这才是中国真正崛起时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