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太史公曰:“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那么司马迁去过的涿鹿,究竟在哪里呢?
文丨金宇飞
摘要:《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的涿鹿,就是位于桑干河流域的河北涿鹿,即“涿鹿之战”发生之地。
根据徐旭生的考证,蚩尤“为山东、河北、河南三省接界处的一个氏族”,结合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分析,认为包括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和大司空村类型在内的仰韶文化,它们可能都是同一个氏族炎帝神农氏的遗迹,而仰韶文化大司空村类型当为蚩尤遗迹。
根据苏秉琦的认识,红山文化有可能是黄帝轩辕氏的遗迹。考古资料显示,桑干河流域的若干古文化遗址,存在有红山文化层叠压在仰韶文化层之上的现象。这表明了在桑干河流域一带,出现过红山文化取代仰韶文化的事实,推测即与黄帝战胜炎帝的传说历史相关。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惯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涿鹿之战是《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的,发生在黄帝与蚩尤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因为发生在涿鹿之地,后人便称之为涿鹿之战。

一、涿鹿之地探讨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太史公曰:“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史记》作者坦言自己曾亲自去过涿鹿这个地方。那么司马迁去过的涿鹿,究竟在哪里呢?
北京大学的王北晨研究后发现,《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代全国只有一个涿鹿县,位于上谷郡内。上谷郡,就是今天河北省宣化县,宜化县距离涿鹿县仅有40公里。当时上谷郡的管辖范围,相当于今天的张家口市。
上谷郡由来已久,战国时属于燕国的管辖地,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仍然设上谷郡。到了汉代,同样沿袭了秦的旧制。因此王北晨认为,既然汉代全国只有一个涿鹿县,那么,作为汉代朝廷史官的司马迁,“北过涿鹿”考察的就应该是上谷郡的涿鹿县。
王北晨的研究是有依据的,是可靠的。这就确定了司马迁所记载的涿鹿,就是位于桑干河流域的河北涿鹿。
也有一些学者,依据《太平寰宇记》卷四十六的“蚩尤城在(安邑)县南十八里,其城今推毁”、《续夷坚志》卷四的“华州界有蚩尤城,古老言蚩尤阚姓,故又谓之蚩尤城。城旁阚氏尚多”和《梦溪笔谈·卷三》的“解州盐泽,方百二十里。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尝溢;大旱未尝涸。滴色正赤,在阪泉之下。俚俗谓之蚩尤血”等记载推测认为,山西运城县解镇古称解梁,也曾经称作涿鹿,所以涿鹿之战可能在山西解镇一带,而不大可能在河北涿鹿。
但是,把涿鹿之地放在山西运城的论据显然是不牢靠的。
《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適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自司马氏去周適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蒯聩其後也。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於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靳,事武安君白起。”
“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当始皇之时。蒯聩玄孙卬。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汉之伐楚,卬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昌生无泽,无泽为汉市长。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迁生龙门。”
这段自序表明了,司马迁的祖先早先在周世袭为史官;大约在惠襄之间(约公元前七世纪)迁徙至晋,即今山西中南部;随后分散在赵和秦,赵在今山西南部至河北南部一带,秦在陕西南部的关中。
按《史记·太史公自序》的语气,分散在赵和秦的两家司马氏,是保持着密切联系的。而司马迁生在龙门,即今山西韩城附近。
依据太史公自序可知,自西周至汉的约一千年间,司马氏家族一直生活在今河南中西部、山西中南部和陕西南部等地,而山西运城恰在这三地的交界之处。
而有关涿鹿之战,在《山海经》《春秋左传》中都有提到,表明这是一个在司马迁之前已经流传了好久的传说。如果涿鹿是在山西运城的话,身为史官的司马氏家族是决不可能对近在身旁的重要信息毫不知晓的。
如果仔细考察有关“涿鹿在山西运城说”的来源,可以发现其所依据的古籍文献,几乎都是汉朝以后的作品。
这一现象表明,在汉朝以前,古人所说的涿鹿就是指今河北涿鹿;而汉朝以后,开始出现“涿鹿在山西运城”的说法。尽管如此,涿鹿在河北的认知度始终占主导地位。因此,涿鹿在河北是可以确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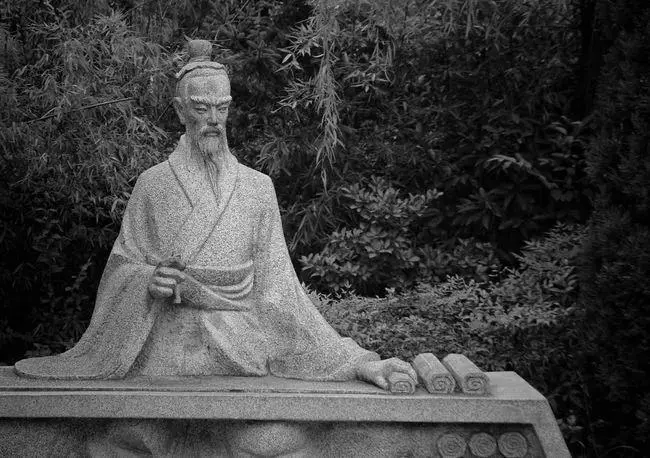
二、蚩尤地望探讨
徐旭生经过考证后认为,蚩尤“为山东、河北、河南三省交界处的一个氏族”。
考古资料表明,在山东、河北、河南三省交界处或其周边地区,已发现有相当多的古文化遗存,延续时间长达几千年。
在这一区域先后出现的古文化遗存,分别有:后李文化(自公元前6500年至公元前5500年)、裴李岗-磁山文化(自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5000年)、北辛文化(自公元前5400年至公元前4400年)、后冈一期文化(自公元前4500年至公元前4000年)、大汶口文化(自公元前4300年至公元前2500年)。
仰韶文化大司空村类型(自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后冈二期文化(自公元前26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山东龙山文化(自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等。这些古文化遗存,是确定蚩尤遗迹的重要实证。
涿鹿之战是蚩尤被打败、轩辕氏称黄帝的重大事件,也是夏以前唯一被记载的通过战争实现改朝换代的古史传说。如果这一事件是真实的,理当反映在考古资料中,也就是在考古学上会表现出是有一种考古学文化或类型的开始或终结。
由于蚩尤是战败或遭受重创,因此上述的某一个考古学文化或类型的终结时间,是推断涿鹿之战时间的重要依据。而在推断蚩尤地望的同时,确定与蚩尤同时期的黄帝、炎帝的地望同样是关键的。
在上述的古文化遗存中,由于后冈二期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终结于公元前2000年前后,这比禹即位的时间都晚,所以不大可能是蚩尤的遗迹,故不予探讨。北辛文化,终结时间约公元前4400年;后李文化和裴李岗-磁山文化,终结时间更早,都太遥远,故亦不予探讨。
至于认为像涿鹿之战这样改朝换代的大事件,不一定会反映在考古资料中,或者不一定表现出是某一个考古学文化或类型的开始或终结,则也不在此予以探讨。
因此,本文主要针对后冈一期文化、大汶口文化和仰韶文化大司空村类型等古文化遗存,来分析和探讨蚩尤的可能遗迹。
首先探讨后冈一期文化。
后冈一期文化,又称仰韶文化后冈类型,主要分布在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年代大约自公元前4500年至公元前4000年。
有不少学者认为后冈一期文化是蚩尤的遗迹。譬如,韩建业认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所代表的是炎帝族系,后冈类型所代表的是蚩尤族系,庙底沟类型所代表的是黄帝族系。黄怀信认为,由王湾三期(龙山文化)上溯至王湾一期以及庙底沟类型而推定后者为黄帝文化。
但是,这样就自然而然地遭遇到了一个难题:黄河边上的这两个氏族,为何把战场设在了远离黄河的河北涿鹿呢?
有的学者为了破解这一难题,就提出了涿鹿是在山西南部的假设。但是,不能因为难以解释黄帝与蚩尤为何把战场设在远离黄河的北方,就把涿鹿之地移至山西。如前所述,涿鹿在河北应当是确信无疑的。
此外,如果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是炎帝遗迹,后冈类型是蚩尤遗迹,庙底沟类型是黄帝遗迹。那么,黄帝的位置是处在蚩尤和炎帝的中间,恰好把两者分隔在东西两边。这样蚩尤与炎帝之间可能存在的任何关系,必须首先要通过黄帝的地盘,这就与许多史料和传说相差太大。
所以,仰韶文化后冈类型或后冈一期文化,不大可能是蚩尤的遗迹。

再探讨大汶口文化。
大汶口文化,主要分布在山东省泰山周围地区。年代约始自公元前4300年,到公元前2500年前后发展为山东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分为3个发展阶段。早期:公元前4300年~公元前3500年;中期: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2800年;晚期:公元前2800年~公元前2500年。
如果大汶口文化或其中的部分阶段是蚩尤的遗迹,那么涿鹿之战时间上的选项也就可能有三个,即: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2800年和公元前3500年。
如果是公元前2500年,这时在其西北方有后冈二期文化(后冈二期主要分布在豫北和冀南一带。由于后冈二期文化区域是在大汶口文化区域和河北涿鹿之间,因此蚩尤要与黄帝在河北涿鹿决战,就必然先要经过后冈二期文化区域。那么后冈二期文化的居民,他们是助蚩尤,是助黄帝,还是保持中立?
如果后冈二期的居民是助蚩尤的,或者就是蚩尤部属,则后冈二期必然会随蚩尤的战败而与大汶口文化一起终结,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如果后冈二期的居民是助黄帝的,或者就是黄帝部属,那么蚩尤在前往涿鹿进行决战之前,后冈二期文化区域必遭大灾,但考古资料并没有证据表明后冈二期遗址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曾发生过灭顶之灾。
除非后冈二期的居民保持中立,但这更难以解释。因此,大汶口文化晚期是蚩尤的遗迹,可能性不大。
如果是公元前2800年,那么蚩尤的对手黄帝在哪里呢?也许只能是同时期的庙底沟二期文化了。同样的难题又来了:黄河边上的这两个氏族,为何把战场设在了远离黄河的河北涿鹿呢?
此外,炎帝又在哪里呢?显然,这些都是难以处理的困惑。而且,公元前2800年之后,大汶口文化进入晚期,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期,这与蚩尤战败者的结局相去甚远。
如果是公元前3500年,那么蚩尤的对手黄帝就只能是当时最强盛的仰韶文化或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还是同样的难题:黄河边上的这两个氏族,为何把战场设在了远离黄河的河北涿鹿呢?此外,炎帝又在哪里呢?
总而言之,大汶口文化也不大可能是蚩尤的遗迹。

那么,还有仰韶文化大司空村类型,是否可能是蚩尤的遗迹呢?
仰韶文化大司空村类型,分布范围集中在豫北洹河沿岸和冀南漳河流域,年代大约自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3000年。
关于仰韶文化大司空村类型,张忠培认为其来源是庙底沟类型,经过钓鱼台类型而发展成大司空村类型61。这一观点已基本为学术界所认同。
如果创造大司空村类型的居民是从庙底沟类型地区迁移来的,那么大司空村类型的居民和庙底沟类型的居民应当具有密切关系或者是有亲缘关系,甚至是同族。
如果大司空村类型是蚩尤的遗迹,那么庙底沟类型就不可能是黄帝的遗迹了,因为没有任何古史传说提到过蚩尤是出自于黄帝的。然而,却有丰富的古史传说和古籍文献,提到了蚩尤与炎帝有着密切关系。《路史·蚩尤传》记载:“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明确地表明了蚩尤的族系,是属于炎帝的一个分支。
如果蚩尤是炎帝之裔,又大司空村类型来源于庙底沟类型,那么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应当是炎帝的遗迹才是。
由于学术界普遍认为炎帝的故地是在渭河流域一带,故有很多学者就把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对应为炎帝的遗迹。
如果大司空村类型是蚩尤的遗迹,那么庙底沟类型就应当是炎帝的遗迹。如果半坡类型是炎帝的遗迹,而庙底沟类型也是炎帝的遗迹的话,那么就会有三种可能性:1.半坡类型不是炎帝的遗迹;2.庙底沟类型不是炎帝的遗迹;3.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都是炎帝的遗迹。
由于不能排除前两种可能性,所以第三种可能性就很值得考虑了。
考古资料表明,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和大司空村类型,由于它们的文化面貌相似,所以被归于同一种文化,即仰韶文化。
同一种考古学文化的不同类型,可能是由不同氏族创造的,但也可能是由同一氏族内的不同支派创造的。如果大司空村类型是蚩尤的遗迹,而庙底沟类型是炎帝的遗迹,又半坡类型也是炎帝的遗迹,则可推断:包括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和大司空村类型在内的仰韶文化,它们可能都是同一个氏族——炎帝的遗迹。而仰韶文化的各个不同类型,则可能是由炎帝或其不同支派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创造和留下的遗迹。
如果仰韶文化是由同一个氏族创造的,则仰韶文化就可以都是炎帝的遗迹。由于仰韶文化历时约两千年,也就是说炎帝时代长达约两千年。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者,……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按《史记》记载,除了提到黄帝分别与炎帝和蚩尤打仗之外,还提到了轩辕氏黄帝是取代神农氏而为天子的。这就是说,轩辕氏黄帝为天子之前,是神农氏为天子。
《帝王世纪》记载:“神农氏,姜姓也。…以火德王,故号炎帝。”这就是几千年来,炎帝与神农氏合而为一的提法,即称之为炎帝神农氏。但近代以来,不断有学者对于炎帝神农氏的并称提出不同观点。
徐旭生认为,炎帝是炎帝、神农是神农,因为古籍所载的炎帝和神农的一些言行显然难以归于一人之所为。刘俊男认为,“炎帝与神农实为两人,炎帝排在神农与黄帝之间”。
周及徐认为,“‘炎帝神农说’流行二千年,然司马迁《史记》无此说,且查检先秦汉初的二十多部文献,言神农或炎帝50多处,神农与炎帝皆不相混,二者的时代特征、重大的行为和事件皆判然有别,是神农与炎帝为先后不同时代之人”。
还有很多学者也提出过类似观点,不再一一列举。总而言之,这一观点在当代的影响已非常大。
关于炎帝神农说,有两个方面的观念值得探讨。其一,炎帝和神农,究竟是同时代的,还是不同时代的。其二,炎帝和神农,究竟是指个人,还是指氏族。
《周易·系辞》记载:“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轩辕……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周易·系辞》和《史记》,应当是先秦汉初最为重要的两部古史文献,而且都一致地表述神农氏之后是黄帝。这些记载可以这样理解,即黄帝、炎帝与神农氏曾经同时过。
目前,无论是把哪个古文化遗存看作是炎帝的遗迹,学者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观念:就是把炎帝看作是指一个氏族,或是一个氏族的首领,或称之为炎帝族。同样,神农氏也是指一个氏族的名称。这与把炎帝和神农看作是个人,甚至是某一个人的观念,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炎帝和神农氏代表的是某个氏族,并且这个氏族延续了几百年几千年那么这期间就会有许多个自称和被称是炎帝和神农的人。也许正因为如此,把不同时期的诸多炎帝、神农的言行记录并流传下来,显然难以归于一人之所为。
因此,如果炎帝、神农之名,被当作是氏族名称的话,那就不能依据古籍文献中有关炎帝与神农的言行不一致,来断定炎帝与神农之间是否毫无关系。
从《周易·系辞》和《史记》中可以看出,炎帝和神农氏,一个是被黄帝打败的,一个是被黄帝取代的。所以,炎帝和神农氏,都是轩辕氏称黄帝之前的氏族,而且还应当同时代过。
如果仰韶文化是炎帝的遗迹,那么与炎帝或炎帝晚期几乎是同时代的神农氏,其可对应的古文化遗存会是哪个呢?而且,黄帝是取代神农氏的,则神农氏的遗迹应当是一个很强大的古文化遗存。
《吕氏春秋·慎势》记载:“神农十七世有天下。”而《尸子》记载:“神农七十世有天下。”南宋的罗泌在其所著《路史》中引《吕氏春秋》也是神农七十世,而不是十七世。
由此可知,《吕氏春秋》中的“神农十七世”之词,应当是在南宋之后才被更改的。至少在南宋以前,《尸子》和《吕氏春秋》都是“神农七十世有天下”。
也就是说,自古至宋,古史传说中的神农氏,都是历时有七十世。
按《说文解字》所释:“三十年为一世”。如果神农真有七十世,那历时需要两千一百年左右,也就是说神农氏有天下大约长达两千年。
神农七十世,相当于两千年,这是古人所无法理解的一件事,因为夏商周三代加起来也只不过两千年。所以汉朝以后几乎是无人提及此事,宋朝以后更是把“神农七十世”改成了“神农十七世”,再后来以至于今,人们几乎已经认为神农仅仅是一个人了。
如果神农氏有天下约两千年,而与神农氏同时代的炎帝,其遗迹为仰韶文化,历时也是约两千年。这一巧合意味着什么?这可以表明,仰韶文化不仅是炎帝的遗迹,也应当就是神农氏的遗迹。
除了仰韶文化之外,还有哪个更强大的古文化遗存可作为神农氏的遗迹呢!因而,炎帝实际上就是神农氏。更准确地说,炎帝出自于神农氏,或是神农氏的氏族首领。如此而言,古人称炎帝神农氏,不但正确而且就是史实。
因此,整个仰韶文化正是炎帝神农氏的遗迹,年代自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历时大约两千年。
苏秉琦认为:“宝鸡到陕县是仰韶文化的中心地区”。而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也正是这一地区中最为繁盛的两个古文化遗存。这片以华山为中心的区域,很可能就是炎帝的中心地区或都城所在。
而蚩尤是炎帝之裔,居住在今山东、河北、河南三省交界处一带。而源出于庙底沟类型的大司空村类型,可以认为正是蚩尤的遗迹。

三、涿鹿之战的史实与真相
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在神农氏末期,轩辕氏与炎帝发生了阪泉之战,然后轩辕氏又与蚩尤发生了涿鹿之战,最后轩辕氏取代神农氏为天子,称为黄帝,由此而导致了改朝换代。
但这一记载流传到近代,出现了诸多置疑:阪泉之战与涿鹿之战发生在何时?与炎帝和蚩尤打仗的轩辕氏又在何处?战场为何竟在北方?
据《史记》记载,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是炎帝和蚩尤被打败,并最终导致轩辕氏取代神农氏的一个重大事件。如果仰韶文化是炎帝神农氏(包括蚩尤)的遗迹,那么仰韶文化的终结时间,所对应的应当就是阪泉之战与涿鹿之战的时间,也就是公元前3000年前后。
据《史记》记载,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后,轩辕称天子,黄帝时代开始。《竹书纪年》记载:“黄帝至禹,为三十世。”三十世相当于九百年。据“夏商周断代工”2000年最新研究结果,推断禹即位之年为公元前2070年。若加上九百年,则黄帝即位之时大约可向前推至公元前3000年了。
考古资料显示,公元前3000年是龙山文化取代仰韶文化的分期界线。龙山文化取代仰韶文化,所表现出的文化突变,比任何同一地域上的古文化遗存之间的变化都要大。
由仰韶文化向前一直追溯至大地湾文化(或老官台文化),而由龙山文化向后一直延伸至二里头文化,这两大系列内的各个古文化遗存之间,都没有发生过像龙山文化取代仰韶文化时那样的巨大变化。而这一巨大变化或文化突变现象,用改朝换代来解释应当是最妥切的。
因此,把阪泉之战与涿鹿之战的时间定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是最恰当的,既符合《竹书纪年》的记载,也可与考古资料相对应。
在公元前3000年之际,即炎帝神农氏末期,整条黄河自西向东分布着各个古文化遗存,西端的黄河上游是马家窑文化,广阔的中部流域是实力最强的仰韶文化属于炎帝神农氏,其中包括大司空村类型——属于蚩尤,东端的黄河下游是大汶口文化。
据《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少皞之墟在鲁”。又有传说少皞建都在穷桑,或叫空桑。而这些地理都在今山东曲阜之北。而曲阜之北、泰山之南,正是大汶口文化的中心地带。因而,很多学者都认为,大汶口文化是属于少腺氏的。
那么,轩辕氏又在何处呢?
根据《史记》作者司马迁的亲历和表述,可知阪泉和涿鹿这两个地方,汉时都在上谷郡,也就是现在的河北宣化一带。既然战场是在北方,那么马家窑文化就不可能是轩辕氏的故地。同样,轩辕氏的故地也不可能是在黄河以南地区。因此,轩辕氏的故地只能从北方地区的古文化遗存中识别。
苏秉琦认为:“考古发现正日渐清晰地揭示出古史传说中‘五帝活动’的背景。五帝时代以五千年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大阶段,以黄帝为代表的前半段主要活动中心在燕山南北,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可以与之对应。”苏秉琦是最先提出红山文化有可能是黄帝轩辕氏遗迹的。
红山文化主要分布于内蒙古自治区东部至辽宁省西部一带,公元前4500年至公元前3000年是红山文化的繁盛期,公元前3000年之后,气候寒冷化致使红山文化衰退。
《太平御览》卷三三九引《兵书》:“黄帝之时,以玉为兵。”《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
《史记·封禅书》记载:“黄帝得土德,黄龙地端见。”“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珣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馀人,龙乃上去。”
传说中的黄帝有尚玉、尚云、尚龙等风俗,这与红山文化出土的勾云形玉佩、碧玉C型龙等玉器,以及所表现出的玉文化,非常对应。

如果红山文化是轩辕氏的遗迹,那么轩辕氏与炎帝、轩辕氏与蚩尤的战场为何远离黄河而在北方的这一千古之迷,也就很容易明白了。
如此,涿鹿之战前夕的形势大致是这样的:
大汶口文化区域居住的是少皞氏,仰韶文化区域居住的是炎帝神农氏,其中大司空村类型区域居住的是蚩尤氏。考古资料显示,大司空村类型的分布区北达冀西北桑干河、大洋河流域。也就是说,公元前3000年之前,炎帝神农氏或蚩尤的族人最先抵达和占据包括阪泉、涿鹿在内的河北桑干河、大洋河流域。
红山文化区域居住的是轩辕氏,涿鹿之战之前轩辕尚未称黄帝。大约于公元前3000年开始,由于科尔沁沙地发生了第一次大规模沙漠化逆转,对红山文化所在区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正是这场大规模的气候变化,导致居住在红山文化区域的轩辕氏开始分批离开故土南下,这样就到达甚至闯入炎帝神农氏族人居住的大洋河、桑干河流域,南北两大氏族在桑干河流域相撞就这样成为了历史。
考古资料显示,桑干河流域的若干古文化遗址,存在有红山文化层叠压在仰韶文化层之上的现象。这表明了在桑干河流域一带,出现过红山文化取代仰韶文化的事实。
而这个事实所表现出的史实与真相是,当红山文化的居民因气候变化等原因南下桑干河流域,而闯入炎帝神农氏的领土,并企图长期占据时,炎帝率领族人来到桑干河流域进行驱逐,这就是《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记载的“炎帝欲侵陵诸侯”之情形。
随后,红山文化的轩辕赶来救援,“诸侯咸归轩辕”。就这样,在轩辕的统领下,在桑干河流域的阪泉之野与炎帝发生了大战,并打败了炎帝。但是,轩辕并没有杀死炎帝。
据《逸周书·尝麦篇》记载:“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少昊,以临四方,司□□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
这里的“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是指阪泉之战后,轩辕氏与炎帝达成了妥协,从而诞生了轩辕和炎帝二后(古时称天子为后),故谓“诞作二后”。
“命蚩尤宇于少吴”,即命令蚩尤的地盘仅限于靠近少皞的地方(大司空村类型的核心区域在豫北冀南,紧邻大汶口文化区域),此命令的要点在于蚩尤的地盘不得远至桑干河流域。
而“司口□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是说当此事传到蚩尤,显然是不成的,蚩尤亲自来到桑干河流域,逼迫炎帝(赤帝)废除协议甚至亲自实行驱逐。
鉴于与轩辕氏之间的妥协,炎帝非常惊恐地把此事通报给了轩辕。这样,轩辕就以“蚩尤作乱,不用帝命”(见《史记·五帝本纪》)为由,又与蚩尤发生了大战,这就是后人所谓的涿鹿之战。
传说涿鹿之战极其艰难,蚩尤勇猛善战,“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屡处下风。后来黄帝之所以战胜蚩尤,是因为得到了玄女等多路神人的帮助等等。
《太平御览》卷十五引《黄帝玄女战法》:“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黄帝归于太山,三日三夜雾冥。有一妇人,人首鸟形,黄帝稽首再拜,伏不敢起。妇人曰:‘吾玄女也,子欲何问?’黄帝曰:‘小子欲万战万胜,’遂得战法焉。”
这个故事虽然有些晦涩,却是一段有关涿鹿之战的真实记叙。首先,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发生在太山。太山即泰山,正是大汶口文化的中心地区。而泰山南麓、曲阜之北,也就是《左传·昭公十七年》中所说的“少皞之墟”的地方。因此,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发生在少皞的统治中心——泰山地区。
其次,所谓“人首鸟形”,应当是以鸟为纪或身着鸟形服饰的少皞的族人。据《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少皞氏鸟名官,…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即少脾氏以鸟为纪。
再次,自称“吾玄女”者,应当是少皞玄鸟氏的一位女性族人或首领。这个故事表述了,当黄帝与蚩尤屡战屡不胜时,黄帝自己或派遣部下来泰山地区与少腺联络,寻求联盟,共商战法,最终联手击败蚩尤。
考古资料表明,仰韶文化之后是龙山文化,而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有着很大的差异,但与大汶口文化之间却有着很多的相似性。譬如庙底沟二期文化与大汶口文化,有很多相似之处;大汶口文化又是山东龙山文化(又称之为典型龙山文化)的来源;而河南龙山文化又受山东龙山文化影响。
这也表明了,公元前3000年之后,大汶口文化的少皞势力开始向炎帝神农氏的仰韶文化故地扩张,这是少皞参与涿鹿之战并作为战胜者的最好实证。
涿鹿之战之后,桑干河流域为轩辕氏所占据,这一地区的仰韶文化被红山文化取代是最好的实证;而少皞也开始了向炎帝神农氏故地进行扩张,深受大汶口文化影响的龙山文化的兴起是最好的实证。轩辕氏(龙)与少皞氏(凤鸟)之间的联盟,开创了一个龙凤呈祥的新时代。
涿鹿之战之后,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时疆域:东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南至于江,北逐荤粥。
如果黄帝时代始于公元前3000年,根据考古资料,这一疆域不仅正好包括了原仰韶文化区域,也正好包括了同时期的大汶口文化区域和长江流域各古文化区域,包括深受龙山文化影响的良渚文化(旧称杭州湾龙山文化)、屈家岭文化晚期或青龙泉三期文化(湖北龙山文)。
如果再加上红山文化区域的话,那么《史记·五帝本纪》所记载的黄帝疆域,恰好把公元前3000年前后中国境内最发达的古文化遗存都包括在内了,这一疆域远远超出了炎帝神农氏的统治区域(即仰韶文化区域)。这充分表明了,黄帝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
(摘自《重庆文理学院学报》 2011年第4期)